
“比行业多走半步,是领头者;多走一步,就可能成为孤岛。”
作者丨赵之齐
编辑丨胡敏
2025年末的算力领域,风起云涌:存储价格翻倍攀升,安世半导体风波余波未平;多家国产芯片公司密集冲击IPO,一纸文书给许多新建的数据中心带来“H20禁令”。
外部环境推动国产算力进程加速,内部的自强意志与之交织,国产算力看似迎来最好的窗口期,实则面临一场关键考验——
这波汹涌而来的产业“流量”,它能接住吗?
对于目前国产算力来说,最难的一关不在实验室里。中科可控董事长聂华说道,实验室里电阻电流、计算主板等产品做到100%国产化并不难,真正的挑战,在实验室之外:
如何让供应链稳定?如何攻破生态壁垒?如何做到完善的工业设计?这些归根结底是一个命题——如何让国产算力真正跑起来?
当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多还停留在纸面上时,聂华和他的团队,已是少数把实验室成果推向产业的探索者之一。
聂华从业二十多年,原本立志在中科院研究所做研究,却“误打误撞”进入产业界,从参与国内高性能计算机研制开始,走上了一条更艰难的道路——投身国产C86产品生态的产业化进程。
见证过国产算力几次浪潮的他,如今对于生态、供应链等落地的艰辛,已深有体会。
会面那天,北京的秋天已是一片金黄。刚刚获得“王选奖”的聂华,穿着蓝白条衬衫和深蓝色西装外套,坐在房间中央的沙发上。他说话时,目光常会注视着提问者,镜片后的眼神平静、谦逊。比起“总裁”,他更像一名科学家,或者工程师。
在这个收获的时节,他讲起推动国产算力落地的跋涉与征程,像复盘一场跨越二十年的长跑。国产C86生态落地的漫漫来路,就这样在叙述中渐渐显影。

中科可控董事长聂华
01
先选成熟的技术路线,先享受生态成果
过去二十年,是国产算力觉醒的年代。
觉醒也意味着混乱、未知,在当时,聂华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是:从众多技术路线里,选定一条坚守的路线。
2016年前后,国产服务器芯片在全球市场份额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国际出口管制的暗流逐渐涌向产业;国内信创仍在试点阶段,由阿里发起的去IOE(IBM主机、Oracle数据库、EMC存储)正蔓延至金融行业。飞腾、龙芯、申威等多条路线的产业化仍在酝酿,直到“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采用申威的处理器,才让国产CPU真正在世界上崭露头角。
那时,国产CPU创业者们心中都憋着一股使命:
坐上桌,占据一席之地。
2017年,中科可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技术出身的聂华作为董事长,起初的关键任务之一,是带领可控突破高端整机的核心技术。
当时国产CPU路线已百花齐放:飞腾经过x86、SPARC等指令集探索,最终选择ARM架构,华为鲲鹏也基于ARM V8架构;海光与AMD达成技术授权协议,获得x86架构授权;龙芯、申威则进行自主指令集研发,后起的RISC-V阵营也准备萌芽。
眼花缭乱,可控起初也尝试了多种路线,但在这之中,聂华逐渐感受到:想要快速切入当时的国产市场,必须要有非常突出的一点:要么是有性价比,要么是用起来方便。
在产品规模化还遥遥无期的年代,谈性价比显然太早,于是答案逐渐明朗:与主流生态x86计算指令相同的国内自研体系C86,自然成为首选。
但,选定这条路后,周边质疑声四起:
那个年代的硬伤是,一提到国产、信创,大家会一股脑想把一切国外事物剥离开。自主指令集或减少依赖外国标准的系统,成为看似更“完美”的选择。
而基于x86架构自主研发出的兼容体系C86,则常被认为是“换壳的x86”。有些人,甚至因为C86可以装Windows系统,就直接把它定义为国产“假替代”。
尽管知道这种“卖菜刀等于杀人”的逻辑并不合理,但本着发展自主可控信念的团队,也害怕被定义为“不够国产”。面对这类指责,团队当时不得不选用一款无Windows驱动的显卡:
使用这款显卡的用户,如果强行安装Windows,就只能使用640×480的低分辨率的“象征性显示”。用起来很不方便,很多用户就会放弃安装。
聂华感到有些无奈,笑评那是不得不“自废武功”以做出的生存妥协。
现在回头看,他依然觉得,坚持C86生态的兼容落地,是当时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
C86和x86在计算指令上相同,最明显的好处是“可以直接享受历史上生态分工带来的成果”,直接对接Windows、Office等。
在聂华看来,装上Windows后,上层SQL Server、Oracle、国产数据库等安装,就不用太担心了。并且,即使不专门特别优化,这些软件也已经能跑出接近满意的性能。
在那个国产算力尚未完全跑通的年代,C86几乎是以“高铁模式”破局——引入国外先进成果,快速迭代,与国际水平持平。
但发展至今,也开始面临尴尬与被动:这种“在兼容中成长”的模式,也意味着一旦上游生态发生变化,国产体系将产生震荡。
聂华观察到,最新版的Windows和C86已逐渐有些脱离,随Windows底层系统接口快速演进,兼容适配的成本不断上升,若要维持应用指令集的深度兼容,代价不小。
他已经在考虑,未来从“绝对兼容”转向“相对适配”,只在应用层上保持兼容性。
但C86的优势不止于计算指令,它与x86的核心差异在于:内部构建了独立的安全处理器。
这在当时并非显性卖点——在国产技术发展还未坐上牌桌的那个年代,安全,远不是大众最关心的话题。
02
“开放”意味着“不安全”?
有一年,聂华在网安中心作报告时,方滨兴院士提过一句:“我们的输入法也可能影响到安全。”
那句话像一枚钉子,扎进他心里。
后来,在另一个大会上,聂华重提类似观点,现场一片哗然。观众朴素的不解是:这不过是老百姓用的输入法,怎么可能会有安全问题?输入法也要谈安全,那大家以后怎么用电脑?
在人们还沉浸在外来技术带来便利与惊叹的年代里,强调安全,似乎是一件“唱反调”的事情。但对此已有判断的聂华,仍然坚持着手探索。
参与过国产高性能计算机研发的他,起初想复刻当时的“垂直整合”模式,这种理论上最安全的模式——
计算机行业默认的分工模式是:硬件、操作系统、数据库等都分给不同的人做,软件层也基于当时的操作系统进行开发。
看似和和美美,但一旦出现技术对抗,或有“链主”角色主导对抗时,这种分工就会被打破。
有见及此,大家探索高性能计算机时,便出现了一种“垂直整合”的形式:做硬件的人,同时也懂软件,在交叉融合下打破原有技术边界。
然而,当中科可控开始准备着手探索时,难题接踵而来:
首先,是在人力上实现的困难:垂直整合要求研发者既要熟悉系统结构优化的软件编写,也要熟悉底层硬件环境,对人才要求高,增加的工作量也不容小觑。
并且,根据某一系统优化的应用,一旦市场转移,就要移植到新的硬件或系统上,面临从零开始的重复工作量。
这笔账怎么都算不下来。
种种考虑下,聂华带领中科可控选择了生态开放这条路——让各类厂商都能基于C86路线开发验证,由此,减少重复的底层开发。
然而,随后潮水般涌来的声音就是:你怎么证明你是真的安全?
一方面,当时市场认为,越封闭的系统相对更加安全,因为开放意味着多样化、不那么受控——这一担忧与技术市场长期以来面对的开源与闭源之争如出一辙。
另一方面,C86虽然是在x86上生长起来的,但毕竟还是年轻的架构,漏洞不那么清晰明确,难以建立用户信任。
聂华要面对的,是人们认知的惯性。
但如今回忆起来,他当时没有特别去对外“自证”,只是持续坚持开放这条路线。
一直到2019年,产业内某个尚未进入市场的国产芯片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给行业敲响了警钟:这份原本限定于军事领域的清单,正在向产业延伸。
此后,随着国产算力高速发展,难以打破的生态壁垒与高昂的异构迁移成本,成了横亘在所有人面前的新难题。
到这时,行业才真正意识到:安全的本质,不是封闭,而是可控。
“一定要领先于别人半步到一步,先做性能最好、最稳定的产品;但做完后,要敢于把这些所谓的产品设计开放出去,支撑更大的生态”,聂华说。
回头看,他又一次选对了路。
03
“一群亚健康聚在一起,肯定不健康”
聂华至今仍记得,当实实在在触碰到C86处理器时,冰凉的金属质感传递到指尖,他脑中只剩下一个声音:
怎么真正让这枚C86处理器,在产业里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那时的国产CPU整机,多停留在实验室或政府、科研等封闭试点场景:难量产,更难被用起来。
大家都在喊信创替代,但大企业没有把业务押注在国产整机上的风险容错空间,中小企业则没钱、也没场景去搭载国产CPU整机。
CPU企业很多专注于架构和指令集、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整机厂商则关注性能指标和成本控制。没有统一标准,没有验证体系,没有一个角色有足够的动力,从供应链视角把各环节粘起来。大家不看好国产产业链的聚合,行业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一群亚健康聚在一起,肯定不健康”。
没人真心做C86产品推广时,坚定相信这条路线的聂华团队冲在了第一线。
他带队打了好几场硬仗:
实验室不够,那就自己建——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可以做CPU长周期可靠性测试的实验室,他带领团队组建高水平实验室,测试芯片在各种场合下的稳定性;制定功能对比体系,与当下最好的产品对比验证。
生产线不精,那就全自动化——当时国内设计能力提升很快,但制造与验证链条的支撑远远滞后,他带领团队引进全自动的生产线,来提高加工精细度。
工业设计不行,那就补上这门课——当时很多整机,在外观工艺、结构合理性、散热布局上等各方面都落后于国外产品,这也是可控重视的领域。
后来,中科可控获得了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智能化生产线设备自动化率已达95%,自动数据采集率和在线检测率达100%;今年,旗下的高端工作站产品还获得了德国红点奖。
但聂华回看时,在所有做过的事里,花费最多精力的还是供应链。
他记得邬江兴院士在会议上说过一句话:
“对于做企业的,你不用说自主可靠配套率是95%还是99%,只要有1%的供应链断链,你就交不了成型的产品。”
哪怕是电源模块或风扇芯片这样的小部件,一旦上游停供,整机项目就可能延期甚至报废。因此,从上游联合实验室,到全程的质量监控,再到构建完善的销售体系——每一环都要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稳下来。
这个过程并不好做,要和上游的芯片、存储、板卡厂一起,共同验证每项参数。“敢大胆采用国产化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光是付出勇气,还有大量供应链管理方面的工作”,聂华希望做到的,是帮助上游厂商,一起解决国产产品功能、可靠性、性能、供应链等问题,让国产C86生态链条更稳定。
发展到第八个年头,如今,中科可控更倾向于退居幕后,作为“强链补链”的角色。
“一觉醒来发现了苹果落地?倒没有这个感觉,做了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才走到今天。”
聂华轻轻说出这句话时,身后窗外是满树金黄,是秋天,收获的季节。就像如今已经在数十个行业系统中稳定运行的中科可控整机,它也走入了收获的季节。
04
余韵:仍有科研梦的企业家
“你义无反顾地去到了企业。”
“你选对了方向。”
“你没有去做科研,但获得了事业的成功和股权的激励。”
聂华现在常常听到周遭这样的赞赏,好像他的生命路程是某个充满命定感的决策的产物。
但每每听到这些,他内心都会响起一个声音:那是你们的视角。
刚刚毕业的他,其实希望成为科学家。
祖籍山东的他,似乎骨子里也追求一种稳定、踏实的生活。他在毕业后去到中科院研究所,拥有事业编,本以为生活就会如此过下去。
但那是中国科研体系剧烈重构的年代。研究所起初还是“一个团队、两块牌子”,既是企业、又是事业。后来,所长李国杰开始推动企业和事业剥离,很多人来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
聂华本想继续作为一名科学家,可到自己选择时,名额已满。就这样,命运的风轻轻一推,他从实验室走进了企业。
当科学家和当工程师,大有不同:科学家追求的是创新,但工程师需要更沉稳地面向应用,踏踏实实做工程,远非标新立异。
“做产业,可能领先半步就够了”,这是技术出身的聂华,在产业里凝练出来的体悟。技术领先太多,没人敢用;产品推太快,生态跟不上。多走半步,是领头者;多走一步,就可能成为孤岛。
回看一路上每个路线选择的节点,中科可控都做出了对的决策,但聂华始终很谦虚,认为背后的推手是时代、而非自己:
“当时我们很小,选对了路对产业的影响并不大。今天和过去不同,当我们有一定产业影响地位的时候,又选对了路,这时候就拥有了‘放大器’”。
回想刚入行时,CPU处理器在聂华心中还充满了神秘色彩:“一个芯片占了机器接近一半的成本,而且比同质量的黄金都贵”。
回头看已经走了这么远,他直言:“不敢想象30年前和现在,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0年,上海超算中心刚刚落成,聂华在项目中见到世界第十的计算机,还只有8T算力。
如今,一块GPU芯片的算力就能超过8T。四十多个机柜的轰鸣,廿载浓缩进指尖的一片硅片。算力的跃升,也悄然丈量着一代工程师的青春。
专题介绍
2023 年来,智算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但两年过去,国内智算企业的生存状态如何?在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中做了哪些新探索、又面临什么新挑战?智算行业的未来还有什么想象空间?本专题与一众智算领域的先锋从业者对话,回顾近年智算行业在技术与商业上的拓展实践历程,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即便身处行业气候更迭之际,从业者们凭借智慧与韧性、怀揣对智算未来的坚信,开辟多样化发展路径。对此专题感兴趣的从业者,欢迎添加微信 Ericazhao23 共同参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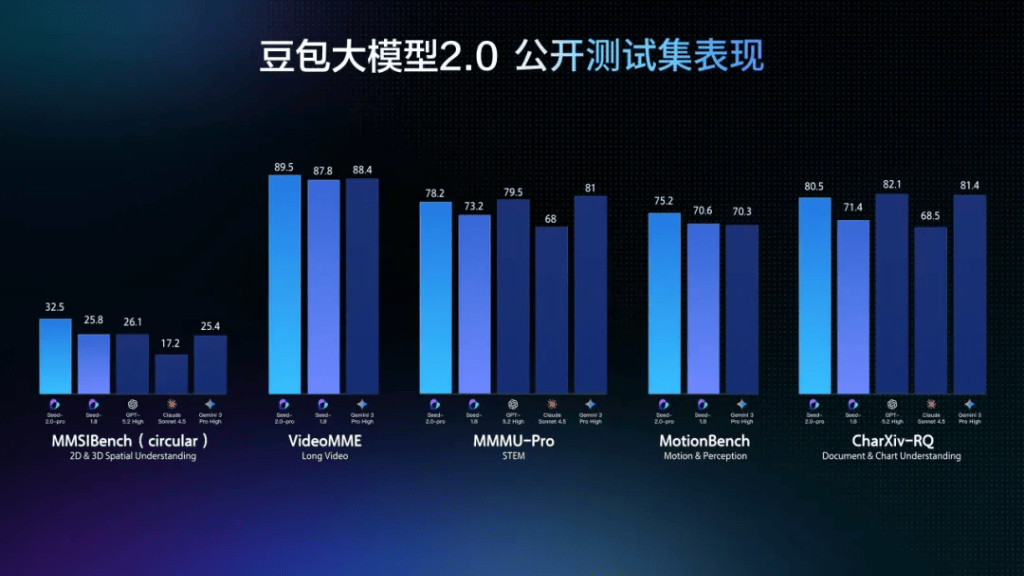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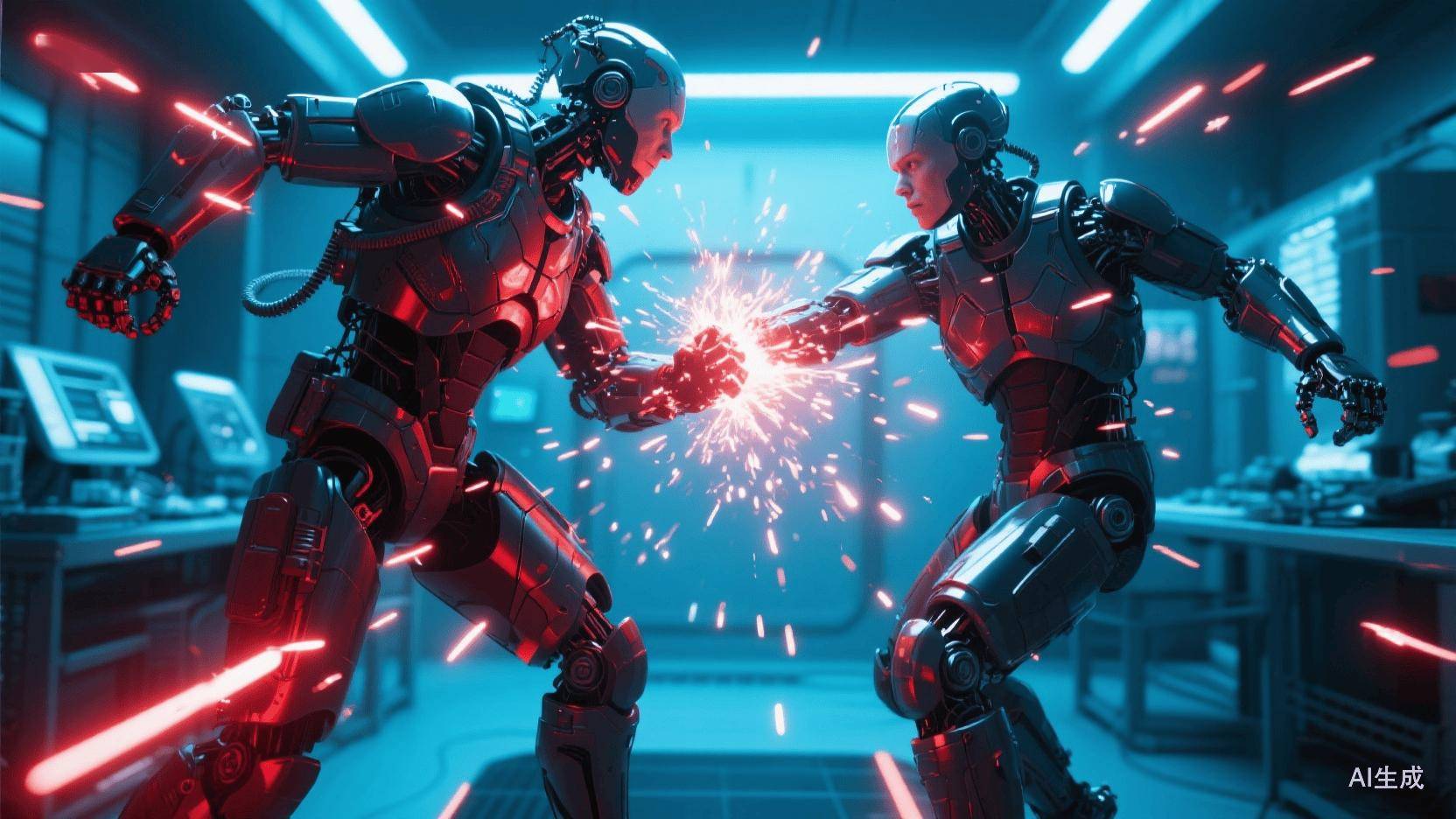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