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 2025 年 12 月 12 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的技术、创新与合作伙伴关系局(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s,TIP)宣布启动一项名为“Tech Labs”的试点计划。

图丨相关公告(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名字,背后却可能是美国联邦科研资助体系近几十年来最具实验性的一次转向。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该计划预计在未来五年内投入最高 10 亿美元,向那些在传统大学体系之外运作的独立研究团队提供每年 1,000 万至 5,000 万美元不等的大额、多年期资助,旨在通过团队化方法应对国家科学优先事项,例如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关键材料、半导体制造和生物技术。
理解这项计划的意义,需要先回顾美国联邦科研资助体系的基本架构。
1945 年,二战刚刚结束,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当时担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曾统筹调配全美三分之二的物理学家参与战时科技攻关,他向时任总统杜鲁门提交了一份著名的报告,标题叫《科学:无尽的前沿》。

图丨万尼瓦尔·布什(WikiPedia)
这份报告指出,联邦政府应当持续资助基础研究,但主要通过大学里的个体科学家来进行,让他们自由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政府则保持“一臂之遥”,不过多干涉具体研究方向。这种模式强调的是研究者的自主性和好奇心驱动,它催生了 NSF 的成立,也在此后近八十年里定义了美国联邦科研资助的基本范式。
这套系统运作得相当成功。战后美国科学的辉煌,从雷达技术到条形码,从多普勒雷达到 DNA 分析,从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到互联网的雏形,都可以追溯到这一体制的支撑。但问题也在逐渐积累。最核心的一点是:能够推动重大突破的科学活动形态,已经和 1945 年不太一样了。
那时候,一位教授带着几个研究生,配上一些基本设备,就能做出世界级的成果。但今天的前沿科学,无论是粒子物理、蛋白质结构预测还是先进材料,越来越依赖大规模的数据集、紧密协调的大型团队,以及持续多年的机构性支持。
2012 年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需要一台耗资数十亿美元的粒子加速器、数十个国家的数千名科学家协作,论文的作者名单长达好几页。Google DeepMind 开发的 AlphaFold 诞生于一个拥有海量计算资源和稳定机构支持的团队。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HHMI)旗下的珍利亚研究园区(Janelia Research Campus)用了数年时间,一个神经元、一个突触地绘制出果蝇的完整大脑接线图,这种规模的持续协作远非任何单个实验室所能独立完成。
然而,美国联邦科研资助的主体结构仍然围绕着小额项目拨款转。《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在 NSF,大约三分之二的研究经费流向大学里获得小额资助的个体研究者;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这一比例往往超过 80%。
NSF 的平均资助额大约是每年 24.6 万美元、为期三年,而且申请者常常需要提前精确预测自己将要进行的研究内容,并花费大量时间应对行政流程。科学家们普遍反映,他们把接近一半的研究时间花在了合规和经费管理上面。
一些敏锐的慈善力量早已开始填补这个缺口。最典型的例子是前谷歌 CEO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他妻子温迪·施密特(Wendy Schmidt)资助的一系列项目。2021 年,他们支持成立了一个名为 Convergent Research 的非营利孵化器,专门培育一种叫做“聚焦研究组织”(Focused Research Organization,FRO)的新型机构。

图丨埃里克·施密特(WikiPedia)
FRO 的设计借鉴了创业公司的组织形式,有明确的技术目标、设置里程碑、由类似 CEO 的人物领导一个全职团队,但它追求的不是商业利润,而是能够加速整个领域进步的公共品,比如关键数据集、新型科研工具,或者某项大幅降低后续实验成本的基础技术。
这些项目通常有 5 到 7 年的期限,每个获得大约 2,500 万至 7,500 万美元的总资助,而非学术界的小额拨款。
FRO 这个概念最早由两位科学家在 2020 年通过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FAS)发表的一份政策备忘录中提出,作者是萨姆·罗德里格斯(Sam Rodriques)和亚当·马布尔斯通(Adam Marblestone)。
他们当时的核心论点是:美国政府现有的 R&D 资助机制在应对那些需要高度协调、团队作战、产出公共品的项目时,存在一个结构性盲区。学术界的激励结构偏向个人署名和论文发表,不利于系统性的团队协作;商业公司鼓励团队合作,但不鼓励生产无法快速变现的公共品。结果就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例如微纳加工、人类基因组学,美国正在被那些更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赶超。
过去几年里,FRO 模式在慈善资助的支持下取得了不少进展。马布尔斯通目前领导的 Convergent Research 已经孵化了 10 个 FRO 项目,涵盖脑图谱绘制、非模式生物研究、海洋碳循环建模、数学证明软件以及低成本天文观测等多个领域。
据 Convergent Research 官方介绍,这些早期 FRO 已经发布了世界上最大的“药物靶点相互作用图谱”和全球海洋碱性增强效率地图等重要数据集,将蛋白质组学的性价比提升了 27 倍,并开发出支撑 AI 辅助数学证明的软件。该软件所孕育的行业里已经出现了估值达到十亿美元级别的独角兽公司。

(LinkedIn)
但慈善毕竟不是可以无限扩展的资源。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在研发上的支出接近 2,000 亿美元,这个量级是最大型私人基金会也无法企及的。如果新的科研组织模式要真正改变美国科学的运作方式,联邦资助体系就必须跟进。
这正是 NSF 这次宣布的 Tech Labs 计划所尝试做的事情。根据目前发布的信息征询书和官方声明,Tech Labs 将向那些在大学官僚体制之外运作、拥有运营自主权的独立研究团队提供资助。这些团队由全职的研究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追求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也就是那些有可能重塑甚至创造整个技术领域的成果。
与传统的学术产出(论文和数据集)不同,Tech Labs 的目标是让团队拥有足够的资源、财务跑道和独立性,能够将关键技术从早期概念或原型推进到可以吸引私人投资、实现规模化部署的商业可行平台。
NSF TIP 副主任埃尔温·詹查达尼(Erwin Gianchandani)在声明中表示,随着科学挑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依赖跨学科专家团队的协作,美国必须扩展其科学资助工具箱以适应新形势。Tech Labs 将让那些“经过验证的科学家组成的创业型团队”获得追求突破性科学的自由,而不必频繁地被申请经费所打断。
有意思的是,这项计划的出台时机似乎兼顾了美国两党的关切。共和党方面对让联邦研究经费更多地流向大学之外表现出兴趣;民主党方面则希望看到《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的后续成果落地,并推动资金尽快拨付。
通过资助独立研究组织,Tech Labs 或许可以绕开一些关于大学间接成本和机构管理费用的棘手争议。就在本周,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乔什·哈德尔(Josh Harder)和共和党众议员杰伊·奥伯诺尔特(Jay Obernolte)联合提出了一项两党立法,呼吁将类似的团队制资助模式引入 NIH。
Tech Labs 计划以及它所代表的更广泛趋势,实际上也折射出科学创新格局正在发生的一种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来自产业界和大型科技公司。
过去十年里,一些最令人瞩目的科学突破并不是诞生在大学实验室或国家实验室,而是出自企业的研究部门。Google DeepMind 解决蛋白质折叠问题只是其中一例。OpenAI、Anthropic、Meta 的基础研究团队正在定义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 AI 的前沿。Nvidia 不仅生产芯片,还在自动驾驶、药物发现、数字孪生等领域搭建平台。这些公司能够调动的计算资源、数据规模和工程人才密度,是绝大多数大学院系难以望其项背的。
这当然带来了另一层担忧:如果前沿科研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商业巨头手中,会不会加剧权力的集中?会不会让公共利益让位于股东回报?那些不能快速变现的基础研究会不会被边缘化?这些问题都真实存在,但它们指向的解决方案,恐怕不是简单地回到战后那种让教授们各自为战的模式,而是需要资助体系发展出新的工具,在团队协作、产出公共品方面与产业界形成互补。换个说法,这是在抢回一部分科研组织模式创新的主动权。
FRO 的提出者们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罗德里格斯在最近的采访中强调,FRO 机制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可以聚焦那些“深度处于商业化前期”或者“以开源和公共品为导向”的领域,这些正是私营部门不太擅长或者没有足够动力去做的事情。
一个做得好的 FRO,可能在几年时间里把某项关键实验技术的成本降低一两个数量级,从而让后续无数的学术研究和商业应用都能受益。这种基础性的、乘数效应式的工作,是学术界碎片化的小额资助难以支撑的,也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研发不太愿意承担的。
当然,将这套模式引入联邦资助体系,会面临不小的文化冲突。现有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机制强调的是谨慎、共识和可预测性,而 FRO 式的项目往往需要冒险,需要赌非共识的想法,需要赋予项目负责人较大的自主裁量权。
马布尔斯通在接受 FAS 采访时提到,虽然 Convergent Research 对旗下所有 FRO 都进行过广泛的同行评议并获得了宝贵的反馈,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评审意见如何被使用,以及评审者和项目官员是否真正理解这类雄心勃勃、有时甚至显得离经叛道的项目的本质。
他建议采用“被赋权的项目经理”模式,做法类似 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用以推动 FRO 项目的遴选,让单个有眼光的项目经理能够押注那些尚无共识的尖锐想法,而不是让一切都通过委员会的稀释。
另一个实践层面的建议是:NSF 不仅应该资助单个的 Tech Labs 项目,还应该考虑支持那些负责“孵化和监督”多个 FRO 的元级别组织。Convergent Research 本身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它为新成立的 FRO 提供运营支持、稳定的治理结构、最佳实践和社区网络。新的潜在 FRO 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摸索,可以借助那些已经趟过一遍的人的经验。
Tech Labs 计划目前仍处于信息征询阶段,更具体的资助细节预计要到 2026 财年才会公布。与此同时,NSF TIP 还将发布另一个配套计划 Tech Accelerators,聚焦于特定的国家优先技术领域,为团队提供更多样的入口来降低风险、加速技术向市场和社会的转化。
不过要强调的是,Tech Labs 并不试图取代传统的个人项目资助,其在培养下一代科学家、支持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方面仍然不可或缺。NSF 此举更像是在现有工具箱里增添一件新工具,一件专门用来应对那些需要大规模协调、长期投入,但又不适合商业化路径的科研挑战的工具。
放到中国语境里,Tech Labs 这种把“组织方式”和“资助机制”当成技术问题来优化的思路或许也能对我们有所启示:对于那些需要长期工程化投入、又很难立刻商业化的共性底座任务,或许更适合用多年期资金支持少数全职团队,允许里程碑式迭代,同时把可扩散的公共品产出写进评价体系。
国内已有新型研发机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探索,但下一步真正考验的是能否在合规与效率之间重新划线,让团队获得接近产业节奏的用人、采购与协作空间,并在知识产权与开放共享之间形成可执行的平衡,避免平台成果要么过度封闭、要么难以持续运营。
至于 Tech Labs 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目前还很难判断。联邦资助体系的惯性、同行评议文化与创业式组织逻辑之间的张力、如何筛选出真正有潜力的团队而非仅仅是善于包装的申请者,这些都是 Tech Labs 在落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但无论成败,它或许会为未来各国思考两件事先行探路:如何在大学与产业之间补齐那层面向公共品的“公共研发中间层”,以及如何用公共资金更有效地催生可扩散、可持续的技术底座,而不是只留下零散的项目与短期的热度。
参考资料:
1.https://www.nsf.gov/news/nsf-announces-new-initiative-launch-scale-new-generation
2.https://fas.org/publication/focused-research-organizations-to-accelerate-science-technology-and-medicine/
3.https://fas.org/publication/tech-labs-announcement/
4.https://fas.org/publication/nsf-supercharge-independent-tech-labs/
5.https://www.wsj.com/opinion/science-funding-goes-beyond-the-universities-d7395da3?st=W2toh5&reflink=desktopwebshare_permalink
运营/排版:何晨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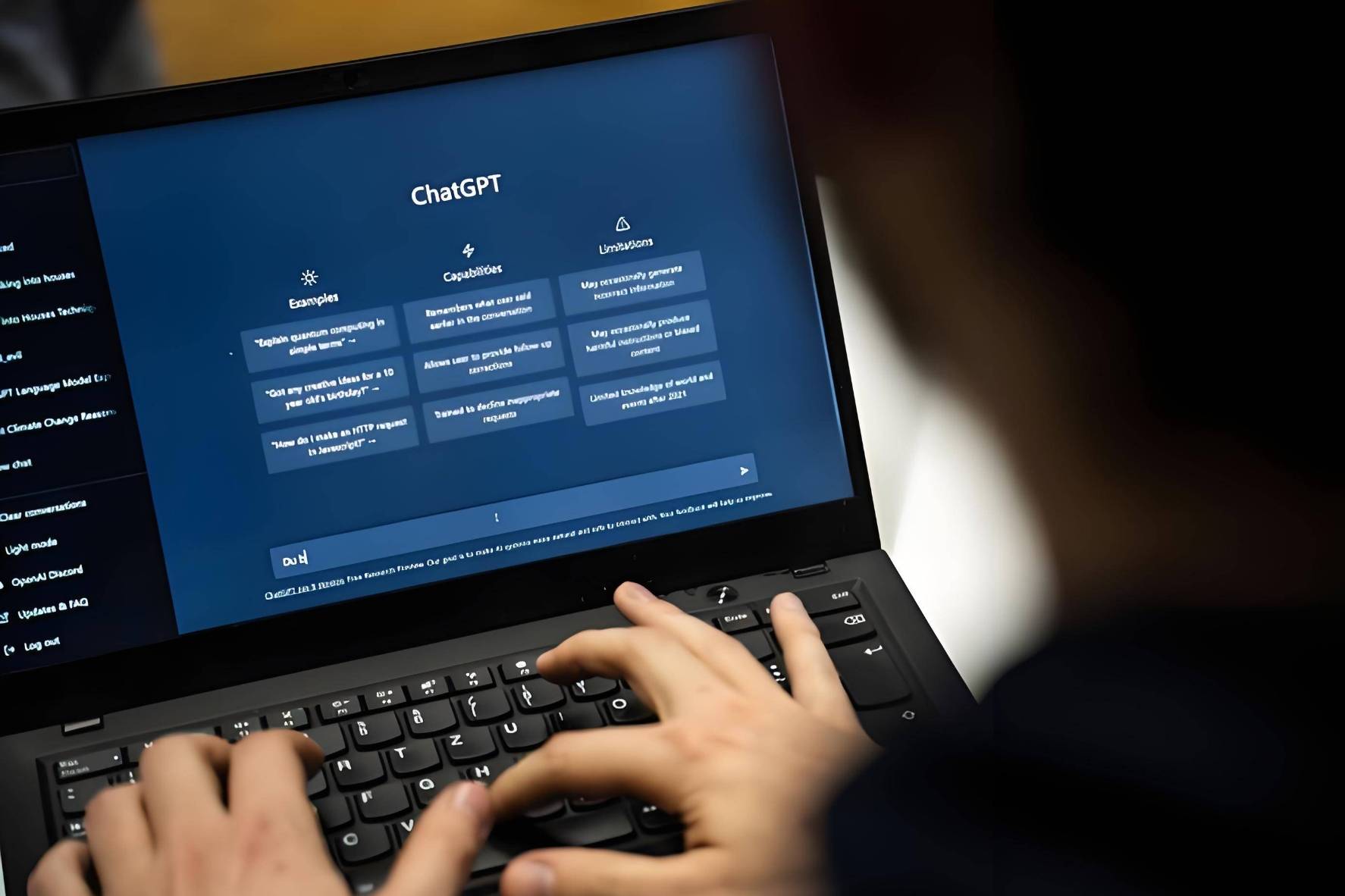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