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智驾供应商如何从规则崩塌中练出 “神奇的模型”。
文丨宋玮 郭瑞婵
如果不离开大疆,青年教授沈劭劼大概率不会遇到 “喝红的还是喝白的”“要不要跪着满足所有需求”“账上只够发三个月工资怎么办” 这种完全不属于工程世界的难题。
但这恰恰是卓驭这家公司的起点。
2024 年 9 月 27 日,沈劭劼带着 1000 多名员工搬离了大疆深圳总部 “天空之城”。这一天,他正式告别被视为工程天堂的 “温室”,走向资源有限、竞争残酷的现实世界。
大疆出身,既是光环,也是枷锁。
卓驭一出生就站在聚光灯下,被放进 “地大华魔” 的坐标里。但也长期活在巨人投影之下——大疆以产品为中心,而卓驭必须学会以客户为中心;大疆内部天然的资源池,让分拆后的卓驭在销售、客户关系等能力上几乎从零起步。工程底子很强,商业肌肉几乎空白,这是它矛盾又特殊的起点。
卓驭就像一个天赋极高、但缺乏社会经验的学霸,需要在市场里重新习得生存之道。
今年 11 月,它从大疆绝对控股的团队,变成由一汽、大疆和管理层共同治理的 “无实际控制人” 公司。国资委以 “链长” 方式推动一汽入局,新一轮融资超 36 亿元、估值 120 亿元。这标志着卓驭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完成。
至此,这家公司才算从温室走入旷野。交易前后,沈劭劼对《晚点 LatePost》回溯了卓驭的三次关键转向:
- 从大疆体系内的团队,走向独立的共治结构;
- 从 “写规则写到绝望” 到删库重练,彻底切入数据驱动;
- 从 “大力出奇迹” 到 “巧力出奇迹”,用最小代价解决行业最难的两件事——因果推理和低频数据生成。
沈劭劼目前也是 HKUST-DJI 联合创新实验室创始主任,获香港科技大学终身教职。他是过去十年亚洲无人机与自主系统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力量之一。
在这次访谈中,他不仅复盘了从大疆走向行业前线的十年;也首次以工程师视角揭秘了特斯拉 FSD 的真正精妙之处;以及一家智驾供应商如何从规则崩塌中练出 “神奇的模型”。
从大疆温室到太空之旅
晚点: 你们最初诞生于大疆内部一个神秘项目,代号 1609,我听说 1608 和 1610 分别是造车和激光雷达。
沈劭劼:其实叫 BR1609,BR 是 basic research,1609 就是 2016 年的第九个预研项目。类似的预研项目有好几个,自动驾驶、整车车控、激光雷达,都有人在做。
晚点: 为什么不造车?
沈劭劼:讨论过,但很早就停掉了。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 “自动的车”。去造车有点像是为了一盘醋,包了一盘饺子。
晚点: 从大疆车载到卓驭科技,为什么要分拆,谁提的?
沈劭劼:最开始肯定是大疆的决策,我没有权力决定分拆。2022 年下半年我们定了要拆,然后用了 2023 年一整年时间去想——到底要拆得多干净。
后来两个因素推动了 “拆干净”:一是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二是卓驭业务逐渐偏离大疆主航道,偏离越远,在内部推进任何重大决策,请示和审批耗时会越来越长,长到比团队把事情做出来的时间还久。
晚点: 当时业内都在议论,分拆是因为大疆无法忍受卓驭的亏损。真实情况是什么?
沈劭劼:亏损肯定是有意见的,但不能用 “忍受/不忍受” 这么简单的方式去描述。
我们之前没意识到这个业务这么难赚钱,最开始还有点幻想——看能不能靠近大疆的毛利率,后来发现连靠近的希望都没有。
晚点: 2024 年 9 月 27 日,你们从大疆天空之城总部迁出,离开的那一刻心境如何?
沈劭劼:有点像《三体》里人类成为太空人类的过程,末日之战后五艘飞船逃了出去,突然发现没有家了,回不去了。还到了一个资源不足的地方,五艘船,但资源只够两艘生存,必须得灭掉三艘。
我们从 0 到 1 在温室里成长,分拆后最现实的压力——是钱。当时正在做第一轮融资,分拆当天融了 15 亿,但搬出来前几天只到账了一部分,只能撑小几个月。你能想象吗?上千人公司被拆出来那一天,账上只有不到 5 个亿。
晚点:汪滔会不会说,“如果没钱了,随时来找我”。
沈劭劼:没有,约定就是要自给自足。
晚点:有什么是你出发时没预料到的?
沈劭劼:“大疆不会是卓驭的第一大股东” 是出发时没预料到的,但在今天看是必然的。
很早就有消息说美国商务部要发布 “50% Rule”:已在实体清单上的企业,其控股公司会被视为同样受限的关联方。此前预计的生效时间(注:该规则现状是推迟一年实施)是今年 9 月。
基于这个约束条件,大疆一定不能是卓驭的第一大股东,同时我们要在极其紧迫的时间搞定这件事。找一家公司能接手这么大的股份,同时这家公司最好是有产业背景的,一汽是最合适的。
晚点:今天一汽已经是卓驭的第一大股东。是否还有其他选择,比如把股权拆散,引入多家战略投资方,每家持股 20%?
沈劭劼:我们是一家估值过一百亿的公司,假如真引入四五家股东,我要怎么在 9 个月之内完成这个事儿?
晚点:业内今天会觉得你们被一汽收购了。
沈劭劼:从来不是卖身或者收购。公司有三层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管会。经管会由我负责,自由度比之前在大疆体系里更高;股东会,一汽约 35%、大疆 34%,团队是第三大股东,没有谁能单方面控制公司。
晚点:一汽会派人参与日常管理吗?
沈劭劼:不会,他们不介入日常经营。
晚点:两家强势大公司股权相当,这种结构会带来什么问题?
沈劭劼:一汽和卓驭已经合作两年多,不是突然买股的关系,而是长期磨合后顺势推进。从董事会结构,一汽有 5 席,其他加起来 6 席,这是一个共管结构。
这个动作来自国资委层面的产业布局,一汽以 “链长” 的角色主导构建智能汽车产业联盟。本轮我们融了约 60 亿人民币,一汽投了超过 36 亿,足够支撑公司进一步发展。下一步的计划就是上市。
晚点:所有智驾公司,是不是最终宿命都是被车企收购?
沈劭劼:其实不是宿命,而是阶段性困局。今天智驾公司的困局在于:投入和收入极度不匹配。
根本原因是大家造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半成品。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产品什么时候跨进成品。如果智驾能 “破 2 到 3”( L2+ 到 L3),那一刻消费者对你的认知会瞬间提升。定价逻辑不再是 “占汽车 BOM 成本多少”,而是 “它帮我节省多少时间、释放多少注意力,我愿意为它付多少钱。”
晚点:你在大疆带无人机飞控团队,做的是成熟的 ToC 产品,为什么要做这么苦的 ToB ?一个企业家曾评价,所有进入 ToB 的天才最后都会变得一言难尽。
沈劭劼:在大疆十年,我们一直想做一件事——造一台真正厉害的机器人。它不是某个具体产品,而是一种 “科技之美”——优雅、强大、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智能体。
Frank 和我的学科背景都是无人机,我们认为无人机和自动驾驶在底层逻辑上很接近,本质都是 “移动智能机器人”——这是我们心目中的皇冠。目标没变,但为了把这件事做成,你得去做很多不在计划里的事。
有点像,为了干成这件事,只能多干点别的事。
开窍了!我们终于练出了神奇的模型

晚点:国内智驾跟进端到端技术路线,已经持续两年了,从 VLM、VLA 到世界模型都试了一遍,你们的进展如何?
沈劭劼:我们也摸索了很长的时间,也曾经自我怀疑,但大概两个月前我们开窍了,我们稳定训出了好几个很神奇的模型。
晚点:炼丹成功了?
沈劭劼:以前更像是拿机关枪乱扫,有能打中的,但对数据分布、数据配比、训练方法、各种 loss(损失函数,用来追踪模型输出的错误程度),都是模糊的。
直到最近模型的训练在往洲际导弹的方向发展——火箭很少整机试射,靠的是把每个零件单元测试、论证清楚,再组装成一个复杂系统。我们开始搞明白模型的训练动态(Training Dynamics),也就是网络结构、数据结构、训练策略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旦搞明白,你发射出去的导弹就能按轨迹飞,不会中途散架。
现在无论我们的中算力还是高算力方案都有质变,有一点 FSD 的味道。客户试 Demo 时会直接说:这条路别人过不了,你们能过。
晚点:这属于你的 Aha moment (顿悟时刻)?
沈劭劼:就是那种工程上的开窍状态。这一两个月我心情好很多。说实话,我今年年初状态应该是最差的。
晚点:差到什么程度?
沈劭劼:其实是从 2024 年 10 月 14 日那个决定开始——在快一年的预研之后,我们这一天全面转向端到端,极端点讲就是把原来交付客户的规则代码全删掉。这等于告诉所有人:我们以后只有端到端,没有规则了。
最开始的模型不成熟。客户端有交付压力,后端产出节奏又非常飘忽。前线交付团队会说:“你给我这是什么垃圾?” 那几个月组织都像高压锅,压力巨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像样的模型。
晚点: 为什么一定要删代码,不能像华为那样慢慢切吗?
沈劭劼: 必须删、断后路。因为我们没有两线并行的资源,只有一个韧性很强、执行力很强的团队。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整个团队都有这个信念。我们当时写规则写到很绝望,解决一个问题会冒出十个新问题,工程上进入 “接近悖论” 的状态。直到纯数据驱动被验证可以不靠人工兜底也能跑起来,一下变干净了,所以我们直接删库重练。
晚点:去年写规则写到绝望,又在分拆公司,有没有想过干脆别干了?
沈劭劼: 没有。我是科技乐观主义者——我始终相信,无论技术问题多难,人类都能解决。
原子弹那么抽象的东西,人类都能搞出来。在原子弹之前,大家没想过还能用 “质能转换” 这种方式去释放能量,爱因斯坦提出质能方程后,人类最终把那个完全抽象的理论变成了现实。相比之下,驾驶这个任务一点都不抽象,每天都在现实世界发生。
晚点:但理想 2024 年初就行动了。你们不是号称技术领先吗,为什么没抓住机会 “遥遥领先”?
沈劭劼:我们是传统机器人学派,基本假设是 “物理世界的模型是我建立的”,对规则有执念。而数据驱动完全反过来:不建模,你用数据来学模型。
这个认知转变需要时间。说白了,打不过就加入,也得先承认打不过。2024 年 10 月 14 号往前一年我们做的事情都是,科学地说服自己真的打不过。
晚点: 我跟你的团队聊,他们很想拿第一,觉得自己值这个第一。他们说,“要做一个屌爆了的东西”。
沈劭劼:是,而且我们看到了那个第一的东西是什么样子。
前段时间特斯拉的 AI 副总裁在 ICCV 上做自动驾驶的分享,我看到了一个真正漂亮的架构。它是由一群同时懂物理世界、懂驾驶、懂计算机科学、也懂神经网络的人共同设计出来的体系。不是一个由公司领导者说,“我要做 VLA,所以你们就必须做出来 ” 的东西。
晚点:是群体智慧的涌现,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
沈劭劼:特斯拉做出了一个很朴素、很务实、能闭环的工程体系。它让我们重新理解了 VLA。
以前业内谈 VLA 有一个隐含假设:这是一个巨大黑盒模型,靠大力出奇迹,模型够大、蒸馏够狠。但这种路线在工程上会有问题,成本也无穷大。
特斯拉给出了另一种方式:巧力出奇迹。它仍然是 VLA,但不是黑盒,是由若干个可解释、有分工的模块组成。它把行业最难的两个问题——因果推理、低频数据生成,用极低代价解决了。
你把它的架构拆开,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些问题,本来就应该这么解决。
晚点:我看完的疑惑是,特斯拉主干还是传统端到端(模仿学习),VLA 只是外挂模块,并非以 VLA 为核心。为什么特斯拉被认为在自动驾驶上最强,而它的架构却不够先进?
沈劭劼: 端到端(模仿学习)本身有两个问题:无法覆盖低频场景(没有数据就无法模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缺因果推理)。
有两条路来解决。一条路是李飞飞说的世界模型——Video in、Control out(输入视频、输出控制信号),理解物理世界的因果关系,理论上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这是一个充分非必要条件,代价极高,三四年不一定做完。
另一条路是保持端到端主干不变,用世界模拟器生成虚拟的低频数据,再用强化学习来做后训练——听起来完美。但现实是:要生成足够真实的虚拟数据非常难。如果真能做到,等于世界模型就被我们训出来了。
所以关键问题变成:怎么在不造 “超级世界模拟器” 的前提下,让模型获得因果推理能力?
大语言模型给出了答案:用自回归架构,不断叠 token 实现推理。只要我让模型能一步步推演动作结果,它就能理解因果关系,也能覆盖低频场景。
我们的 AWM(Action World Model ,动作世界模型)就是这么来的。它是基于自回归的决策规划模型——不是看到输入立刻给动作,而是内部推演多种可能路径,理解因果,再生成决策。想明白这一点,再往后就变成:我们怎么用最低代价去设计这样一个架构。
晚点:你的同事刘思康跟我说,他看完特斯拉的分享感叹,“为什么特斯拉都已经搞出来了,我们现在还在搞?” 你觉得还差哪一步?
沈劭劼:我们和特斯拉思路 90% 一致,但特斯拉补上了一个关键环节——强化学习所需要的虚拟数据如何生成。
答案就是 3D Gaussian Splatting(3DGS,高斯泼溅),把真实场景重建成既可训练、又可渲染、可微调的 3D 表达。
3DGS 不需要像《模拟城市》那样从 0 开始模拟世界,而是基于真实数据做微调。举个例子:一个行人慢慢走过来,3DGS 能微调成走快一点、走着走着停下,你就能在高频数据上生成大量基于这个场景的低频和长尾数据。因此解决了没有低频数据,虚拟数据难生成的问题。
特斯拉的设计精妙之处在于,3DGS 是集成在原生的感知网络里的,不需要额外跑一个庞大的世界模拟器。在车端还是走传统链路:感知输出 — 决策规划 — 出轨迹。但在云端可以用相同数据做微调、生成一堆新数据训练,有点 “黑客帝国” 的感觉。
晚点:你说你们离特斯拉就差那 10%,这个差距本质上是因为什么?
沈劭劼:可能我们蠢一点?(笑)
晚点:既然有 “巧力” 路线,为什么大家还往义无反顾往 “大力” 走——更大的模型、更激进的蒸馏、更高的算力。
沈劭劼:走 “巧力” 路线的公司不止我们一家,只是大家不太愿意在公开场合讲。你看,光向你解释清楚这条路线,我们就聊了半个小时,公关场合没人会这么讲——“模型够大” 这种叙事听起来就更厉害。
晚点:那究竟谁领先谁落后,卓驭在什么位置?
沈劭劼:我不太愿意回答这种问题。如果必须说,我觉得我们是中国前三。还有一些技术观比较正、路子比较正的公司,比如 Momenta、地平线、文远,我们盯得比较紧。
晚点:主机厂不在这个列表里?
沈劭劼:不在。
晚点:什么时候能真正验证你们这条路线可以跑通?
沈劭劼:消费者能看到的都比较滞后。真正的竞争发生在主机厂的技术评审、项目竞标、Demo PK——每家公司都会把最先进的东西拿出去跑。
这些非公开的场合,业界的真实排名会比较清楚。那个排名通常跟市场 PR 呈现的顺序完全不同。
头部玩家差距只有三个月,胜负在 Anytime
晚点:卓驭有一段时间被称为 “价格屠夫”。你们从低算力低成本切入,让一款 10 万元不到的 A0 级电动车拥有智能驾驶功能。
沈劭劼:我们第一天就是软硬件结合,它天然会带来性价比——特斯拉就是这个逻辑的极致。但说我们 “只会做性价比”,这有失偏颇。要是你问我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我一直在找一条线。
晚点:一条线?
沈劭劼:就是最低成本,但能让用户 “安全使用、普遍好用” 的那个临界点——这是大疆基因——大疆无人机从来不是最便宜的,但它在那个价格上做到了极致体验。
我几年前说,辅助驾驶成本应该是整车售价的 3%-5%。这个观点今天也没变。
晚点:刘思康(卓驭行为智能部负责人)说,你们每年都会评估去年做的东西是不是还有改进空间。一旦可以继续挖,就不会放弃。
沈劭劼:大疆文化有个词叫激极尽志,就是把一个东西做到极限,做无可做。
外界有个误解,觉得我们 “迷恋做小算力的事”。其实不管大算力还是小算力,如果团队判断它在工程上可行,我们就愿意花时间和资源去试。
晚点:今天你们为什么还在迭代 TDA4——一个被认为算力过低、早已过时的平台。最近还把城区领航跑在了 TDA4 上,坚持它的意义是什么?
沈劭劼:说白了,就是不甘心。
我们最早推中算力方案拿了不少订单,但它能卖,是因为它没有对手,行业里没人做。后来端到端带来了数据驱动范式的切换,其他厂商的方案赶上来,我们原来的方案落伍了——这也正常。所以坚持迭代不是纯商业驱动,而是工程师的执着。
我们觉得自己还没碰到那条线——既然有可能做到,为什么要放弃?
晚点:你有没有想过,这条路可能永远也够不到那条线?
沈劭劼:想过,但后来发生了关键变化:我们长期压榨算力和传感器,让我们在转向端到端后发现——实现同等能力,我们的算力需求比行业低很多。
我们在 8650 上实现的性能,能和 Orin X 一样。我们不断对网络进行压缩部署,压着压着发现端到端网络也能部署在 TDA4 上,所以就做了 OTA,让五菱、捷途、大众油车的性能都显著提升了。
最近一个月,随着数据清洗、训练方法的变化,我们看到了质变,一些能力已经真正跨过那条线了。
晚点:你们很幸运,在强标落地时刚好对上了国家要的方向。卓驭在压榨算力和传感器上的路线,正好是解决 “低成本条件下也能稳定过线” 的问题。(今年 9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要求关键安全场景必须稳定识别、AEB 等核心功能必须达标、冗余和数据记录必须可靠。)
沈劭劼:强标以后,所有口水战结束了。你能过,就是合格产品;过不了,就不合格。
未来会出现两个档位的产品:一是用最低成本过强标的方案;二是无限靠近 L3/L4 的最强性能方案,强标只是最低要求。前者就是我们一直想找的那条线, 以前模糊,现在被法规清晰勾勒出来了。
晚点:这真是一个冒险的决策,当年你们 all in 中配,很可能追不上最新技术,又被芯片性能提升反噬。当时行业都觉得卓驭掉出了 “地大华魔” 第一梯队。
沈劭劼:如果你是想问,我们当时应不应该把中配、高配一起做,我会说应该。没有同步开启高算力方案,是决策失误,在客户最需要城区领航的时候,我们没有,导致丢了客户。
但排位赛每天在变,市场宣传会让人觉得谁声量高、谁声量低,但声量不足不是致命的。只有技术真的不行、你自己也知道不行的时候,才会崩盘。
晚点:遭遇戴维斯双杀(Davis Double Kill)。
沈劭劼:当你发现大家都是半斤八两,头部玩家之间真实差距不超过三个月,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晚点:当年你们和华为车 BU 几乎同一时间起步,后来你们眼看着它跑到了前面。那段时间你怎么给自己和团队解释?
沈劭劼: 正面硬刚华为,无论资源还是业务形态,大家心里都有数——军团战上很难刚过他们。
但我得想清楚:要怎么把心目中那款智能驾驶产品做出来。这条路可以是 “极高市占率 + 极高溢价 + 极高声量”,也可以是完全相反的路径:一个默默无闻的供应商,把事情做成了。我们现在介于两者中间。
晚点:你们也开始做高算力平台。起步更早的玩家已经在前面,你们要怎么追?
沈劭劼:我们不是重新开始做一套高算力,而是在统一架构上向上延展。从 TDA4(中算力),到 8775(舱驾一体),再到 8650 和更高算力平台,我们的核心架构是一套。这套架构在不同算力上都能成立,并能规模化复用。
我们有两个高算力方案产品:一是 L3/L4 方案,两块 Thor 芯片,加上自研激目前向感知系统和知周补盲雷达;二是舱驾一体方案,用高通 SA8797,把 VLA 融在统一架构。
我们是业内唯一能同时提供大算力 L3/L4 方案与舱驾一体方案的供应商。而且,因为工程能力强,同样芯片在我们手里能跑出更高的效率。所以英伟达、德州仪器都愿意给我们更低的价格。
晚点:你们模型负责人陈晓智说,自动驾驶要做成,必须是软硬一体,当时行业里只有卓驭和华为这么做。华为做芯片、激光雷达、4D 毫米波雷达。你们呢?哪些硬件会做、哪些不会?
沈劭劼:我们不造车、不做芯片,也不碰毫米波雷达这种已经相对成熟的硬件。
激光雷达我们会做,原因很简单:一是价格已经下探到 1500 元级,进入可规模化使用的区间;二是工程门槛迅速下降,正往相机模组化的方向发展——接收器芯片化,发射器与镜头组装即可。三是我们对应该如何安装和使用激光雷达(即舱内激目系统)有自己的理解,这个理解很难通过外采零部件实现,我们要自己对它验证。
这样我们原来做相机的团队就能直接上手,从立项到样机只要四个月。强标后,对纯视觉的压力更大,我们现在更愿意给客户推荐带激光雷达的方案。
晚点:Momenta 曹旭东认为,明年城市辅助驾驶就能定格局,国内只剩两三家,你同意吗?
沈劭劼: 不管他说哪两三家,我们肯定在里面——毕竟血条挺厚的。头部几家的差距是以月为单位在波动,真的,别那么自信,智驾模型的进化会像大语言模型一样,哪一家训练出了一个能打的模型,能瞬间把整个行业排序给你翻盘。
我们现在有 50 个已量产车型,定点正在开发的车型也有几十个,是行业头部,而且在油车智驾这个赛道上没有对手。从营收看,我们卖软硬一体,单车收入是同行两三倍。
晚点:最近特斯拉 AI 前负责人 Andrej Karpathy 提出了 “9 的征程”。在一个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系统中,每提升一个数量级的性能(从 90% 到 99% 再到 99.9%)难度是恒定的。到 L4,还有漫长征程。
沈劭劼: 如果你两年前问我什么时候 L4 会实现,我会说不知道,或者用行业黑话回答你——“永远 N+5”,你无论什么时候问,我都说 5 年后会实现。
现在我会说:Anytime。
行业从规则时代迈入数据驱动时代,真正决定胜负的是训练体系里的数据管理和对 Training Dynamics(训练动态)的理解:怎么练、怎么配数据、怎么稳定收敛。这些都是秘方,不会公开,但对性能提升极其关键。
整个行业目前状态很像二战时期的 “曼哈顿计划”:美国、苏联、德国都在造原子弹。美国第一个做出来,但回头看,当时它们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自动驾驶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
晚点: 难道不是特斯拉先造出原子弹吗?
沈劭劼:特斯拉也还在路上,现在是质能方程已经出现了,但原子弹还没被真正造出来。
晚点: 字节也在做自动驾驶,它有可能成为黑马吗?
沈劭劼:从 “大力出奇迹” 的框架看,它们是有潜力的。但之前有其他互联网公司做自动驾驶,出了一个挺搞笑的事——它投了很多人去搞,但连一个生产采购都没有,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进行项目交付。
晚点: 你觉得你们和特斯拉自动驾驶的差距,对比豆包和 ChatGPT 的差距,哪个更大?
沈劭劼:都属于那种 “差一点就能看懂” 的状态,不是天差地别。
不受干扰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能产生干扰的东西太多了。参考曼哈顿计划就行,美国第一个造出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受干扰,目标明确、资源集中,这比资金本身还重要。
以前会想万一错了怎么办,后来发现,错了不怎么办
晚点:大疆有 “天才文化” 的土壤。卓驭有吗,如何让这样的土壤形成?
沈劭劼:你得真正尊重那些有能力、有这种文化的人。其次,手不要伸太长。我自夸一下,做这么多年老师的基本技能就是,我很擅长以 “半旁观者” 的角度,引导新人从不懂到一步步变懂。
晚点:你之前提过一句口号,“既要、也要、还要”。现在好像不再说了?
沈劭劼:这是我的锅。过去我执着于 “既要也要”——既想要出货量,又想要利润;既看经营指标,又强调毛利率。听上去美好,似乎团队能在多个目标之间动态优化出一个最优解。但后来发现,这套策略行不通。
除非组织本身专业性极强、具备综合优化的能力,否则任何阶段都应该只有一个明确目标——明确到只要我把这句话放在这儿,任何人都不会理解错。
行业的变化速度太快了,最忌讳的是组织内耗,“既要、也要、还要” 必然带来内耗。现在我更倾向于:保持一个清晰、单一的战略目标,在行走过程中不断正负二十度进行调整。
晚点:现在那个 “单一、明确” 的目标是什么?
沈劭劼: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口号是 “提效能、拓市场、树口碑”——典型的 “既要、也要、还要”。我没有能力让组织同时做好这三件事。现在我们把前两个都删掉了,只剩一句:树口碑。
晚点:如何评价卓驭的人才密度?
沈劭劼:很偏科。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发展不均衡,因为卓驭从大疆内部的研发部门长出来,很多职能是在拆分过程中临时补齐的,甚至拆开前一天还在用大疆共享的资源。
和从 0 到 1 全面搭建的公司比,我们的组织结构是 “先天不对称” 的,这些会在后来体现成短板。
晚点:从一个事业部负责人到一名 CEO,最不适应的是什么?
沈劭劼:当时我从事业部负责人变成 CEO,我的 N-1 变成公司副总,我要快速完成这个心态转换,就像三体里末日之战之后人类的思想转变一样。
但团队里很多管理者心态没转变过来。直到现在还有管理者问我:“这个事情公司是怎么想的?” 在过去,“公司怎么想” 是一个既定答案——上面有一个集团,会给方向,你只要执行。现在当我的 N-1 还在问 “公司怎么想”,这就出问题了。
公司是谁?拆出来这一年,这是一件被反复鞭打的事情。
晚点:大疆是典型的产品驱动,但卓驭是一家 ToB 公司——要靠销售和客户关系活下去。你们在这个文化切换里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沈劭劼:就是我们最弱的那一块——销售,乃至整个前线作战阵型。
大疆是 “以产品为中心”,但 ToB 业务要做起来,必须是 “以客户为中心”,这两种文化在我们这里一直没有很好融合。我一直对搭建技术型销售有执念:能听懂客户的需求,也能从产品侧把价值讲清楚,我们现在还没建起来。
晚点: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的技术型销售吗?
沈劭劼: 我是一个不错的技术人员,但我不是一个好销售,我正在努力。
华为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以客户为中心,我一直在想,对卓驭来说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我们经常遇到一个拉扯:工程师心里觉得 “更漂亮” 的方案,和客户要的方案冲突,怎么选?照着 “以客户为中心” 理解,最后会变成一个很二元的问题:难道要跪着满足所有需求吗?
今年我们终于把这件事想清楚,把那句话改成了:“用户为本,成就客户。” 用户是终端消费者,是我们判断方向的旗帜;成就客户,说得直白点,就是和我们合作的人能把事做成、能升职,我们不坑队友。
晚点:大疆之前有个禁令——销售不能喝酒。你们能喝吗?
沈劭劼:在大疆,我们最开始是能喝的,后面是不能喝的,拆出来之后,我们又变成能喝了。
我不怎么喜欢喝酒,但怎么说?只要别把身体喝出问题来,喝就喝吧。不过白酒我一喝就醉,一百毫升就跪了。
晚点:你从智驾行业里的关键玩家——Momenta、地平线、华为——分别学到了什么?
沈劭劼:Momenta 给我的最大冲击是曹旭东的韧劲——有好几场战斗,你以为他们要输了,但关键时刻都能硬拧回来,他们有种绝不服输的气质;地平线让我看到的是灵活性,策略和路径上的调整速度非常快;华为实话说,一切都是预期之内的强大,它本该是那个样子。
晚点:你是《三体》铁粉,怎么看 “黑暗森林” 逻辑在商业竞争中的体现?
沈劭劼:这里是一个完全透明的行业,透明到和黑暗森林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家的东西都摆在桌面上,我们基本上知道竞争对手在做什么,车企也知道每家供应商什么水平。
晚点:如果都是明牌,你们技术能力又这么强,为什么卓驭还不是第一?
沈劭劼:因为这是体系能力的竞争。大家都看得到彼此的招数,能不能做出来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能看到地平线如何靠芯片国产化绑定主机厂,但我们做不了;还有一些企业的商务手段更丰富,我们也做不到。软件供应商也知道我们怎么靠软硬一体去完成极难的车型适配——比如油车和舱驾一体,他们也做不了。
晚点:卓驭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沈劭劼:最大的优势是团队的笃定和极强的工程能力。
工程能力体现在:遇到难题不放弃、不打补丁,而是把问题真正啃透。这是我们过去软硬一体化积累下来的底子。两个例子:我们在北汽极狐阿尔法 T5 上做的舱驾一体,工程难度极高,但最终效果能跟最头部带激光雷达的车对打。另一个是给大众油车做智驾,在很受限的条件下把性能做得很稳。
接下来几个月你会看到,我们在 32 TOPS 到 1000 TOPS 的不同平台上,都做到了归一化的丝滑体验,这些算力平台的潜力其实还远没挖完。
在技术端,我们组织的内耗很低,这让我们切换之后的加速度非常快。两个组因为方案吵半天、最后人走了的情况——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
以前还会想 “万一错了怎么办”。后来发现,错了不怎么办。宁愿押错,也不能纠结。
不过这里指的仅是技术端啊,其他领域还存在不少内耗,我们还在努力熵减。
晚点:在竞争中最警惕什么?
沈劭劼:内耗,不作死就不会死。

沈劭劼和团队
造高达的人,必须是能熬的人
晚点:你很年轻,1987 年,你的学生评价你是国内机器人顶级专家、亚洲最好的 robotics 老师之一,也是各类顶级机器人期刊的编辑。
沈劭劼:你删去所有顶级的形容词之后,我都认(笑)。
晚点:性格特点?
沈劭劼:严重社恐。
晚点:那讲课的时候怎么办?
沈劭劼:讲课我最怕的不是面对人,而是讲到一半卡壳。比如在黑板上推公式,推着推着,发现公式没推出来,这个是最恐怖的事情,其他都没事。
晚点:你 2014 年 9 月回港科大当助理教授,同一天加入大疆做顾问。10 年后你升了副教授,当上了 CEO。如何能做到学术和创业两条路并行?
沈劭劼:怎么说呢?我的职业生涯第一天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只打一份工是什么样子。但对我来说这不是两条线,而是同一条线:要造一个真正厉害的机器人,必须同时站在学术和工业两个场景里。
晚点:你和汪滔很早就认识?
沈劭劼:我们是李泽湘老师不同阶段的学生。我大一的时候,他研一。后来我去美国读博做无人机自主导航期间,我们一直有保持联系。
晚点: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接去大疆?
沈劭劼:其实我可以反过来说这个问题:我加入港科大是因为大疆。
做学术的主要好处是自由度,2014 年的中国机器人行业,成熟度和人才密度都不如现在,当时学术界的研究或者一定程度的隔离是有必要的,但这个必要性在后来越来越低。
晚点:如果你不来大疆,只留在学术界搞研究,能做出全世界最厉害的机器人吗?
沈劭劼:不能。学校里工程能力不行,而且你也没有获取问题的途径,很多知识相关的碰撞就不会出现,人会变蠢。
晚点:从汪滔身上学到最多的一点是什么?
沈劭劼:看到科技之美长什么样子,以及追求科技之美的那个步伐。
晚点:卓驭如何在漫长发展和激烈竞争中保持初心不变?
沈劭劼:公司是创始人的镜子,创始人不变,它就不会变。保持一个状态:今年的我觉得去年的我是傻子。
晚点:那还好,李一帆跟我们说,今天的他觉得昨天的他是傻子。创业很苦,有没有哪一刻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干这件事?
沈劭劼:其实我最自豪的一个事就是——我很能熬。我属于那种有病也不去看,能一直硬扛到最后的人。
晚点:是否有创业者典型的 emotional roller coaster (情绪过山车)?前一天晚上觉得世界要塌了,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自己能拯救世界。
沈劭劼:INTJ 最不能忍受不确定性,我更多是有一种持续性焦虑,处于 “睡不够、头有点痛” 的感觉:你不喜欢,但你知道,你能熬过去。
我从 Day One 就想造一个厉害的机器人,我们那一代人说 “造高达”,就是这个意思。只要我还为了这个目标工作,我就不会崩。如果哪天有人告诉我,“你去做房地产吧”,我下一秒就崩了(笑)。
晚点:从学术界到商界,这些年让你最意外之事是什么?
沈劭劼:在一个产品没有到 95 分之前,技术和产品之外的因素所占的权重,要远高我们的想象。
晚点:你一直说 “造一个高达”,但你又不做人形机器人。“高达” 对你来说,具体意味着什么?
沈劭劼:我会做下半身,就是 Mobility(移动能力),但我不做上半身。
如果讲更大的愿景,就是:科技以懒人为本。人们不想干的事,都有机械、智能体帮我干掉。 部署于云端的 AI Agent 这种我不懂,做不了。但在 “移动” 这个物理领域——我要把这件事闭环掉,把它彻底做好。
晚点:特斯拉、小鹏都在强调,自动驾驶技术未来可以大面积复用到机器人上。你是否同意?
沈劭劼:在数据驱动的框架真正搭起来之后,这是顺理成章的。我很有信心——未来真正能把这种 “数据驱动型机器人” 做好的一定是这批在自动驾驶里打过仗的公司。
晚点:你们今年 5 月在官方招聘帖里描述了你们的理想候选人,这段话是你写的吗?
“他能够讲清楚自己要什么,而且他有一个故事,关于他为什么想把事情做成——那是他的一段真实生活经历,可能他自己搭了航模,他自己做了一些小机器人,他的手摸过电容、摸过螺丝,他把那个壳遥控起来,看它落在地上炸坏过,也看它成功飞起来过。他对为什么喜欢这个事有非常切肤、非常真实的生活体验。那不是一句话或者一个词语,而是他那个时候的泥土气息、触觉、味觉和那段稠密的生活。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一个把美好的东西带到现实世界的冲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研发的一个本质:去想一些现实生活中没存在的美好事物,然后把它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沈劭劼:这段话不是我写的,但我曾经输出过无数段跟这个类似的东西。我一直相信有一种务实的浪漫主义:看到科技之美长什么样,并且永远不要停止追求它。
题图卓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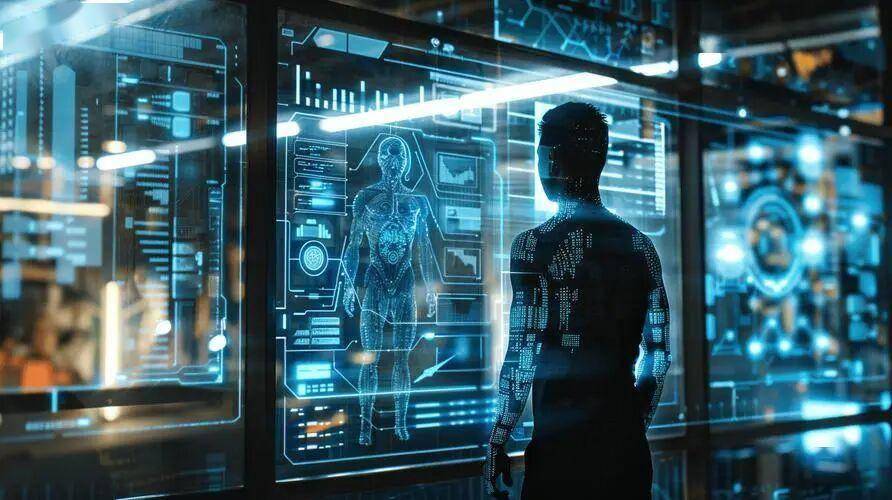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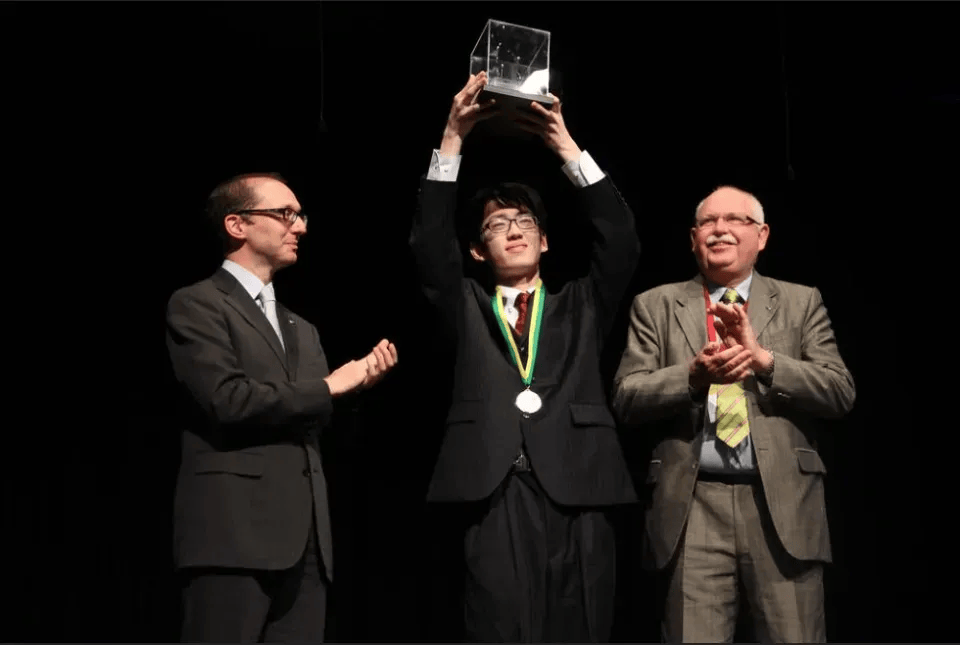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