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 Meta 的营收增长,靠纵容「诈骗」。
作者|徐珊
编辑|郑玄
每年至少 70 亿美元,每天向用户推送多达 150 亿条诈骗广告——这竟然是社交巨头 Meta 惊人的「取财之道」!
近期,外媒披露的一个「惊天大秘密」直指 Meta 光鲜亮丽的营收数据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欺诈性广告业务。
内部文件显示,Meta 公司去年底曾预测,其年度总收入的约 10.1%,大约 160 亿美元来自高风险的诈骗广告和违禁商品广告。尽管 Meta 发言人声称实际数字「更低」,但另一份内部文件却指出,Meta 每年仅从部分诈骗广告中就能赚取约 70 亿美元 的年收入。更令人震惊的是,该公司平均每天向用户展示约 150 亿条具有明显欺诈特征的「高风险」诈骗广告。
更有甚者,Meta 对付疑似非法营销人员的手段堪称「黑色幽默」:要么让他们缴纳足够的高额广告费,要么就等着被列入内部的「诈骗者」报告。这种类似收取「保护费」的机制,让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都变成了一个虚假广告大本营。Meta 内部报告甚至承认一个尴尬的现实:「在 Meta 平台上宣传诈骗比在谷歌上更容易。」
对此,Meta 发言人表示,公司已「足够尽力」,并强调已将用户举报的诈骗广告数量减少了 58%。然而,内部文件却揭示,Meta 曾因将诈骗广告归类为「低严重性」问题而忽略或错误地驳回了高达 96% 的用户有效举报。

Meta 创始人、CEO 扎克伯格 |彭博社
与无下限地狂揽欺诈广告收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Meta 正无上限地向 AI 领域投入天价资本。其 AI 基础建设设施的资本支出指引已升至惊人的 660–720 亿美元。
同时,Meta 还濒临着核心人才齐出走的困境。「卷积神经网络之父」杨立昆在 2013 年加入 Meta 后,一手建立起 FAIR 实验室并推动其成为全球顶尖 AI 研究机构,但今天他也宣布自己离开 Meta 创业。有媒体推测,推动杨立昆离职的原因之一是原本直接向首席产品官汇报的杨立昆,现在需要向 28 岁的 ScaleAI 创始人亚历山大·王汇报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除了杨立昆,基础 AI 研究科学家陈欣磊、研究科学家庄靖尧等至少 14 人跳槽至马斯克的 xAI 公司。此外,新实验室 FAIR 已有至少 8 名员工离职,部分人返回 OpenAI 或加入其他公司。
一边是暗藏污垢的百亿美元「欺诈营收」,一边是动辄数百亿的 AI 基建投入。Meta 究竟如何将其 AI 基建所获得的能力转化为业务的实际收入,以对冲这天价的基础设施成本?而更深层的问题是:在这场由算力、基建与资本主导的 AI 战争中,一家以「社交网络」为核心的纯粹媒体公司,是否真的有必要,下注如此庞大的 AI 基建?这豪赌的底气,是否就来自于那些被其忽略甚至纵容的「欺诈」带来的暴利?
01
「在 Meta 平台上宣传诈骗比在谷歌上更容易」
路透社通过此前未公开的文件勾勒出 Meta 广告业务的一幅「至暗图景」:Meta 的平台几乎每天都在向用户推送多达 150 亿条「高风险」诈骗广告。这些广告会让数十亿用户面临欺诈性投资、非法在线赌场或者是违禁医疗产品的销售风险。而诈骗的方式,不仅限于付费广告,用户每天还会遭遇 220 亿次不涉及付费的「诈骗尝试」,如虚假交友资料等。步步退让下,Meta 的产品已成为全球诈骗经济不可或缺的支柱。
「在 Meta 平台上宣传诈骗比在谷歌上更容易」,Meta 内部研究结论更显讽刺与尴尬:Meta 在打击诈骗方面,显然落后于其主要竞争对手。英国监管机构发现,2023 年所有支付相关诈骗损失中,有 54% 与 Meta 的产品有关,是其他所有社交平台总和的两倍多;而 Meta 自身的研究估计,其平台参与了美国三分之一的成功诈骗案件。
为什么会更容易?这是因为在用户保护和合规方面,Meta 做法显得暧昧且缺乏力度。文件显示,Meta 自动化系统认定必须有至少 95% 的把握确定营销人员存在欺诈行为时,才会禁止其投放广告。对于那些「把握较小,但仍然认为广告商很可能是骗子」的情况,Meta 采取的并非直接封禁,而是实施「惩罚性竞价」,也就是提高广告费率。
这意味着,涉嫌欺诈的营销人员只要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就能继续在其平台上投放广告。这种「以罚代禁」的机制,本质上模糊了平台管理与「创收」的界限,让 Meta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对诈骗行为收费放行的「中介」。
内部文件甚至记录了「高价值账户」,比如说那些支出较大的广告商,即使累计超过 500 次违规记录,Meta 也不会封禁其账户,这无疑是严重放水的行为。
这一切让用户处于极度被动的情况。在 Meta 上,一名加拿大皇家空军的征兵官账号被盗后,黑客用她的名义投放了加密货币诈骗信息,导致她的前同事损失了 4 万加元。尽管受害者及其数十位朋友向 Meta 提交了超过 100 份举报,但该账户仍活跃了数周,无人问津。这并非孤例。一份 2023 年的文件显示,Meta 几乎驳回了用户提交的约 10 万份有效诈骗举报中的 96%。曾任检察官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艾琳·韦斯特直言,Meta 对用户举报欺诈行为的默认回应就是忽略。
面对监管压力,特别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金融诈骗广告的调查,Meta 内部权衡了经济利弊,算好账才选择纵容。一份 2024 年 11 月的文件残酷地指出,Meta 每六个月仅从那些「法律风险较高」的诈骗广告中就能赚取 35 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几乎肯定超过「任何涉及诈骗广告的监管和解费用」,因为内部预计美国监管罚款最高不过 10 亿美元。这意味着,Meta 在短期内从欺诈中获得的收入远超其可能面临的罚款。文件甚至暗示,该公司领导层决定仅在即将受到监管行动时才采取更多措施来审查广告商,而非主动采取行动。
Meta 如今走钢丝般的商业模式,让人不得不质疑其转型的底气与道德基础。如果一家万亿美元市值的科技巨头,需要依靠纵容欺诈来「输血」其 AGI 雄心,那么是否会因为其道德上的缺失而蒙上阴影?
02
赚钱速度不如花的快,Meta 搞 AI 亏大了?
正是带着这种令人不安的巨大矛盾,当马克·扎克伯格在最新财报会议上,以一种近乎宿命般的口吻宣布「我们必须加快进程」,并承诺在 2026 年大幅扩大资本支出时,华尔街仿佛听见了一声熟悉而刺耳的警报。
这一幕似曾相识。就在几年前,他也曾如此孤注一掷,在 Connect 大会上宣布将整个公司的命运押注于「元宇宙」,不仅将 Facebook 更名为 Meta,更是每年投入上百亿美元填向 Reality Labs。两年过去,结果是:股价持续探底,投资者信心降至冰点。
如今,剧本几乎未变,只是主角从「元宇宙」换成了「AGI 数据基建」。巨额资本支出承诺一出,Meta 股价再次应声暴跌,市值瞬间蒸发千亿美元。而与此同时,微软股价仅微跌约 3%,亚马逊和谷歌甚至因上调支出预期而股价上扬。在同行不同市场反应的映衬下,Meta 的处境更显被动。
事实上,自扎克伯格宣布全面转向 AI 以来,Meta 的股价便陷入了周期性剧烈震荡。这个昔日的社交巨头,正陷入一场缓慢而痛苦的拉锯战:一边是扎克伯格想要快速抵达他所坚信的未来,一边是对「画饼」失去信心的投资者们。

MetaAI 基建数据中心|路透社
单从营收表现来看,Meta 本季度交出了一份相当亮眼的成绩单。
2025 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公司营收达到 5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创下历史新高,增长主要得益于广告业务的强劲拉动。更值得关注的是,Instagram 在广告收入增速上首次超越 Facebook,显示出 Meta 社交广告矩阵正从「一枝独秀」走向「多点共振」。此外,Meta 预计 2025 年其在美国的社交广告收入将进一步提升至 789 亿美元。
这一增长背后,AI 驱动的广告平台 Advantage+发挥了核心作用。作为 Meta AI 技术落地的重要载体,Advantage+实现了从广告创建、投放到管理的全流程自动化,不仅能实时诊断投放问题,还可提供精准的优化建议,从而充分释放广告创意的潜力。
为进一步提升转化效率,Meta 也在持续优化品牌转化效率,例如推出「一键直达品牌私信」等功能,大幅简化用户导流路径。可以说,在现有社交广告的玩法体系中,Meta 已将广告投流效果挖掘到相对极致。
数据也印证了 AI 投入的回报:2025 年第二季度,AI 推荐系统的改进使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用户使用时长分别提升 7% 和 6%;而由 AI 驱动的视频推荐系统 Reels,带动视频观看时长同比增长超过 20%,显著提升了广告曝光量。
但站在 512 亿美元营收增长对面的是,Meta 今年第三次上调增长预期,第三季度资本支出指引已升至 660–720 亿美元,主要用于 AGI 数据中心集群的建设以及 AI 人才的变动。

Amazon、Meta、谷歌、微软预计的资本支出|The Information
目前,Meta 首座 AI 数据集群「普罗米修斯」计划于 2026 年在俄亥俄州投入使用,预计将提供至少 1GW 的计算能力。
但正是这类不断膨胀的基建野心,加剧了投资者的忧虑:市场开始质疑,如此庞大的资本投入,是否真能转化为与之匹配的营收增长?Meta 是否真有能力将 AI 基础设施变成一门「好生意」?
与此同时,组织层面的震荡同样令人不安。在经历上一轮重金招揽 AI 人才之后,Meta 近期再度启动组织架构调整,裁员约 600 人,波及 FAIR 前沿研究团队及 AI 基础研究院。这种频繁的团队重组,不禁让外界怀疑:Meta 内部是否已想清楚如何将 AI 与现有业务有效融合?动荡的组织架构,又能否持续支撑真正的技术突破?
在这些不确定因素笼罩下,Meta 的 Llama 模型发展也显得前景不明,难以在短期内看到显著成效。尤其是最新一代开源模型 Llama 4 虽然在开发者社区中获得了一定的采用率,但在多项关键能力的基准测试中,其表现仍显著落后于 OpenAI 的 GPT-4o、谷歌的 Gemini 2.5 等闭源领头羊,甚至在代码生成、复杂推理等高端应用场景中,与同类顶尖开源模型相比也未能建立起明显优势。
而压垮投资者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来自管理层在财报会议上的模糊表态。当被多次问及 AI 与公司未来战略的具体结合路径时,扎克伯格与首席财务官 Susan Li 均未给出清晰回应,反而一再强调「资本支出还将继续上调」。这种只谈投入、不谈路径的沟通方式,无疑进一步动摇了市场对 Meta 战略执行力的信心。
03
不做 AI 基建,Meta 行吗?
股价暴跌的另一大原因是,不少投资者很难理解 Meta 为何如此执着于 AI 基建:因为它既没有像微软 Azure 或谷歌云那样的云业务来承接和分摊巨额投入,也缺乏清晰的路径将 AI 能力转化为实际收入。Meta 的现金流也并非充裕到可以无视投资回报率的程度。
那么,Meta 为何仍要孤注一掷?从现有的公开信息可以推测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争夺「入口定义权」。AI 正在重塑人机交互的范式,未来我们可能不再需要无数独立 App,而是通过一个或几个超级 AI 入口来调度一切。届时,内容与服务的分发权力将高度集中。如果 Meta 放弃自研通用大模型,就等于将下一个时代的「入场券」拱手让给 OpenAI、谷歌和微软——这无异于重蹈移动互联网时代被应用商店「抽成」的覆辙。显然,扎克伯格不愿再犯同样的错误。
第二,延续其「元宇宙」的终极愿景。无论是构建一个开放的虚拟世界,还是打造标志性的元宇宙体验,都极度依赖强大的通用 AI 模型和背后的算力基础设施。从将 Facebook 更名为 Meta 的那一刻起,扎克伯格就已将公司的命运押注于这个未来,而 AI 基建是其不可或缺的基石。
第三,为其硬件战略铺路。自 2014 年收购 Oculus 以来,Meta 在硬件上的探索从未停止。从 Quest Pro 到智能眼镜 Ray-Ban Meta,再到研发中的 AR 眼镜 Orion,其目标始终是在下一代人机交互设备中占据一席之地。在 AI 定义硬件的时代,拥有一个能跨设备调用的自有大模型,已成为其硬件战略能否成功的必要条件。
可以清晰地看到,与谷歌、微软利用 AI 来增强现有业务并平稳过渡到下一个时代不同,Meta 的豪赌,是为了赢得一张通往新时代的「入场券」,一个拥有更多可能性的未来。

Amazon、Meta、谷歌、微软预计的现金流|The Information
然而,这场豪赌的成本极其高昂,尤其是目前 AI 基建的利润正大规模流向上游,英伟达、台积电等芯片巨头接住了大部分订单,而模型厂商则背负着沉重的采购与运营成本。更严峻的是,技术迭代的速度远超以往:云服务商芯片的寿命正从 5-6 年缩短至可能仅剩 3 年,数据中心技术也可能在 5 年内过时,这意味着天价基建投资面临着极高的贬值风险。
在芯片吞噬大部分利润、算力仍显不足的背景下,巨额的资金投入能否换来可持续的盈利,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正因预见到这一点,科技巨头们正积极从别处开拓利润。无论是 B 端的企业服务,还是 C 端的订阅应用,现有的模型厂商们都希望通吃市场,以支撑前期研发投入。Meta 之所以同时押注大模型与 XR 硬件,或许也正是为了开辟多元化的业务线,来为这场关乎未来的生存之战输血。
04
转型之路,为何 Meta 走的困难重重?
当一家科技公司成长为巨头,转型的阵痛几乎成为必然的命运分水岭。顺利者如谷歌与英伟达,总能在技术浪潮转折处精准卡位,乘势而上;曲折者如微软与英特尔,则往往需经历几番试错与重构,才找到通往新增长的道路。
作为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中最年轻的成员,Meta 的成长路径曾被视为典范—,凭借强大的社交网络效应与全球人口红利,它在数字广告的黄金时代实现了爆发式增长。然而,也正是这份「年轻」,使其在判断转型时机与规划路径方面,显露出与成熟巨头之间的差距。
尤其当 Meta 在短短四年内接连启动两次重大战略转向,从「元宇宙」到「AGI 基建」,市场看到的是创始人敢于颠覆自我的勇气,却也暴露出其在战略连贯性与业务协同上的思考不足。投资者与内部团队都难以看清一条清晰可信的增长曲线,反而目睹公司在多个产业尚处早期阶段时,便以巨额投入押注一个难以量化的未来。
可以说,扎克伯格始终在积极探索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但 Meta 整体仍处于一家「年轻公司」的成长探索期——敢试错,却也易摇摆。而通往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征途,注定不是一场短时决战,而是一场关乎耐力、资金与信念的长期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Meta 最需要赢得的,或许不是技术突破,而是投资者的信任。在愿景尚未转化为营收、投入仍不断加码的当下,说服市场继续保持耐心,将极度依赖创始人个人的信誉与说服力,这将是扎克伯格作为领导者面临的最大考验。
*头图路透社
本文为极客公园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极客君微信 geekparkGO
极客一问
你看好 Meta 的 AGI 转型之路吗?
诉讼背后的金额之争!马斯克捐赠 3800万,与自身宣称差超六成
点赞关注极客公园视频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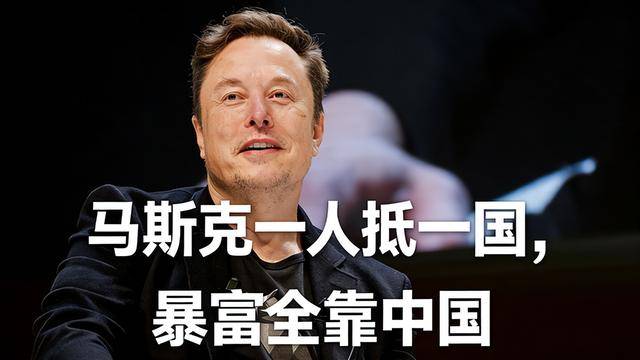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