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把老年人推向右翼
作家与文化评论者埃德·卢克尔(Ed Luker)在《雅各宾》上的一篇评论指出,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社交媒体的有害影响时,65 岁以上的人却在线上消费着日益增多的极右翼内容,而这正在影响现实世界的政治。
在数字世界里,注意力为王,而点击能带来收入,于是人们的社交动态里充斥着由AI生成的“挑衅诱饵”(ragebait,指故意以极端、煽动性叙述激发愤怒以驱动点击与转发的内容)与错误信息。但据《金融时报》近期报道,除了65岁以上的人之外,人们已经走过了社交媒体使用的峰值。

美国华盛顿特区,人们使用手机社交媒体参加活动。视觉中国 图
“无限滚动”(infinite scrolling,页面在用户下滑时自动加载新内容、缺乏停顿点)由前“Mozilla”用户设计负责人Aza Raskin提出,是指社交平台让内容持续刷新、没有尽头的设计。关于这种强迫性消费的心理学研究已将“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指持续消费负面新闻与灾难信息的强迫性刷屏行为)与更高的焦虑和心理困扰联系起来。Raskin对此称:“作为设计师,我知道,只要拿走那个‘该停了’的提示,我就能让你做我想让你做的事。”他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并为自己的发明造成的伤害道歉。
然而,随着社交媒体日益成为“泔水内容”(slop,网络俗语,指粗制滥造、低营养的信息流内容)与“脑腐”(brain rot,网络俗语,指长期沉浸低质内容导致的专注力与思考力退化)的家园,科技作家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将此称为“劣化”(enshittification),即平台在追逐利润过程中对用户体验与创作者权益的系统性破坏与退化,人们也在逐步离开这些平台。
记者兼数据分析师约翰·伯恩-默多克(John Burn-Murdoch)的数据表明,社交媒体使用在2022年达到高点。此后,发达国家成人在社媒上花费的总时长下降了多达10%。平均而言,人们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2小时20分钟。
出人意料的是,转身离开社交媒体最多的是年轻用户。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知名民调与社会研究机构)去年发布的研究发现,青少年对社交媒体的态度高度批判。许多青少年对“在线度日”的风险保持警惕。根据皮尤的研究,大约45%的青少年认为自己在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太多。
这一总体趋势有个意外的例外:65岁及以上的人群正变得“彻底沉迷上网”。
《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称,治疗“屏幕成瘾”的门诊患者中,老年人的比例在上升。英国通信监管机构Ofcom(英国通讯管理局,负责广播与网络监管)的报告发现,65岁以上的人平均每天上网3小时。更令人担忧的是,65岁以上人群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可能性是其他年龄段的两倍,而社交媒体上常见的则是带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色彩的“挑衅诱饵”内容。
在英国语境中,“Politics Home”的研究发现,“改革党”(Reform,英国极右翼政党之一,受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启发)成员以年长、中产、男性为主。他们也更可能通过X(原Twitter)或Facebook获取新闻,而非像其他政党的支持者那样依赖传统渠道。“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美国右翼政治口号及运动,常与特朗普支持群体相关)文化对其叙事风格影响显著。
新右翼对年长男性的激进化,部分由在线错误信息推波助澜。Facebook和X等平台充斥着缺乏监管的“辱骂移民”内容,刻意放大恐惧和偏执,把社会描绘成即将陷入灾难的景象。
此前《卫报》上的一篇文章(作者Ben Quinn)也表示,在Meta取消事实核查员后,外界担忧英国“婴儿潮一代”在Facebook上激进化。
专家担心,Meta取消在Facebook上使用专业事实核查员(fact-checkers,指受过训练、依据可验证来源核对网络内容真伪的专业人员)的决定,将加剧英国所谓的“婴儿潮一代激进化”(boomer radicalisation),指主要出生于二战后婴儿潮时期、现已步入中老年的群体在网络上被极端观点影响、走向激进立场的过程。
早在去年夏天英国发生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所称的“极右翼骚乱”之前,警讯已然敲响:相较于年轻的“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指从小就接触互联网与数字技术、使用熟练的一代人),老年人被认为更容易受到错误信息与激进化影响。根据《卫报》对数百名被告的分析,与2011年骚乱中被起诉者相比,2025年英国骚乱嫌疑人总体更年长,其中多达35%的人年龄在40岁或以上。
随着扎克伯格宣布Meta将以“众包系统”(crowdsourced system,指由普通用户共同提交与评议信息以标注真伪/背景的机制)取代事实核查员,并会推荐更多政治内容,如今外界对Facebook的潜在激进化风险更为担忧。Facebook是许多老年人的首选社交平台。
德蒙福特大学(De Montfort University)学者、欧洲跨国项目“Smidge”(Social Media Narratives: Addressing Extremism in Middle Age,社交媒体叙事:处理中年阶段的极端主义)的首席研究者萨拉·威尔福德(Dr Sara Wilford)说:“这显然是倒退了一步,并伴随各种风险。”
“X可能是Meta所拥抱的‘社区注释’模式(community notes,一种由用户补充背景与纠错、再经群体投票提升可见度的机制)的参考样板,取代专业审核员。但在Facebook上不会以同样方式奏效,因为Facebook非常依赖一个个小圈层或封闭社群。我担心,对于那些可能接触到极端内容的中年Facebook用户而言,分辨真相将变得更加困难。”
反极端主义倡议组织“希望而不是仇恨”(Hope not Hate,英国民间反仇恨/反极端主义团体)也对《卫报》表示,他们担心扎克伯格的宣布是为极右翼人物和团体重返Facebook铺路。在被封禁前,Britain First(英国极右翼组织)尤为善于利用该平台,曾累积200万点赞,一度超过工党(100万)与保守党(65万)。
就犯罪施害者而言,年轻男性仍占多数。然而在这次骚乱之前,围绕“婴儿潮一代激进化”的讨论已被若干案例点燃:达伦·奥斯本(Darren Osborne)在2018年因于伦敦北部芬斯伯里公园(Finsbury Park)的清真寺发动致命恐袭而入狱,当时他已48岁,法官称其是在网上被“快速激进化”。
另一起案件中,安德鲁·利克(Andrew Leak)在2022年向多佛(Dover)一处移民中心投掷燃烧弹,被警方定性为“极右翼”袭击。他时年66岁,随后自杀,身后留下充斥种族主义内容的网络浏览记录。
谈到此次骚乱,“希望而不是仇恨”表示,极右翼在不同平台上的用法各异。该组织研究总监乔·马尔霍尔(Joe Mulhall)总结说:“Telegram用于煽动最极端的仇恨,或有时用于策划。而X用于扩散这些信息。而Facebook往往是你会看到某个团体围绕某个具体事件创建本地化的定向内容的地方。过去三四年里,我们也看到反移民抗议的Facebook群组在组织针对庇护中心的行动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威尔福德表示,她的研究显示,一些年长的Facebook用户常常特别脆弱,原因包括:不愿主动事实核查,以及当信息包装成传统新闻输出的样式时,倾向于信任在线内容。
在卢克尔看来,左翼政治理应去对抗日益影响老年人的社会性孤立。然而,代际鸿沟的扩大让这一任务更为艰难。
社交媒体大规模普及至今已十五年,很明显,这些平台的主要效果之一,是把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商品化,同时让人保持孤立与不信任,这不只破坏了社会政治,而且破坏了任何集体事业赖以生存的纽带。人们生活的社会里,不同世代之间的线下社交正变得罕见。更糟的是,通胀、房租上涨和生活成本攀升,使得维持“线下生活”变得更难、更昂贵。
卢克尔认为,要建立能够真正改善人们生活的社会与政治运动,人们需要把那些已经习惯于数字空间所依赖的孤立与虚假安慰的人纳入其中,需要主动接触那些最愤怒、也最孤独的人。
自助哲学能让我们免于痛苦吗
近半个世纪以来,斯多葛主义这一古老哲学在西方社会重新流行起来,与之相关的书籍层出不穷,甚至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出版产业。近日,哈佛大学科学史系讲师埃里克·贝克(Erik Baker)在文学杂志《漂移》(the drift)发表了长文“我如何学会停止担忧并爱上糟糕的生活|当自助变成哲学”(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My Shitty Life | Self-Help Gets Philosophical)。在对自助产业的哲学化路径进行勾勒后,贝克对斯多葛主义在当下的流行和受到的批评进行了反思。

埃里克·贝克(Erik Baker)
贝克指出,特朗普很早就公开表达他过对于人类成就之徒劳的哲学思考。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访时,特朗普说:“我们在这里活到60、70或者80岁然后我们离去,你赢了,你又赢了,到头来根本没什么意义。”2004年时他对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拉里·金(Larry King)说,“你做节目,做这做那,然后突然间印度发生地震40万人丧生。说实话,都不重要。”2020年竞选期间,特朗普曾经表达想要跳进支持者的卡车“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在今天,抛下一切逃离现实的幻想特别具有吸引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特朗普本人。自他从十年前开始转型成为政坛巨擘以来,作为对既由他引起又以他为症候的混乱的回应,“一切都不重要”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
正如众多社会科学家、民调专家和趋势观察家所观察到的,一种宿命论的情绪日益弥漫在许多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心态中。而应对绝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告诉自己,怀有希望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在这样的氛围中,一系列自助书籍应运而生。自助大师马克·曼森(Mark Manson)继2016年的畅销书《不在乎的巧妙艺术》(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uck)之后,在2019年出版了续作《一切都糟透了》(Everything Is Fucked),敦促人们接受“痛苦是宇宙的常态”。如果读者觉得曼森的作品过于粗俗,那么还有充足的替代选项,从约瑟夫·阮(Joseph Nguyen)的2022年的畅销书《不要相信你所认为的一切》(Don’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Think),到内华达大学传播学教授兼健身网红迈克尔·伊斯特(Michael Easter)2021年的《舒适危机》(The Comfort Crisis),再到莎拉·奈特(Sarah Knight)2018年的《冷静点》(Calm the Fuck Down)……这些自助书籍的共同承诺即帮助读者与失望、沮丧以及痛苦是人生无可避免的部分这一事实和解。
如今,偏爱博学色彩的读者越来越容易在哲学板块找到关于人类有限性的智慧。尽管从哲学中学习如何生活并不新鲜,但在贝尔看来,令人讶异的是,即使是出自学术出版社的学术书籍,也越来越带有明显的启发和指导性质,仿佛哲学的核心任务是指引求学者更好地接受不完美和无意义已经成为共识。自助产业也乐于拥抱哲学概念,众多自助书籍作者都声称自己从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这样一来,人们几乎很难一下子分清楚一本提供人生建议的书籍究竟是哲学著作还是自助书籍。
他进而指出,哲学式的自助常常自我标榜为主流自助潮流加诸现代文化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有毒的积极心态的一剂解药。这种观点不无道理,正如芭芭拉·埃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其2009年的文化批评著作《失控的正向思考》(Bright-sided)中所指出的那样,积极思考——永远期望最好的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梦想,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之一,詹姆斯·克利尔(James Clear)在《掌控习惯》(Atomic Habits)中写道,“获得持久成果的秘密就是不断改进”,该书自2018年出版以来全球销量已经超过2500万册。这类书籍通常使用科学语言或者福音派基督教语言,前者的代表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的《终身成长:重新定义成功的思维模式》(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2006),后者的代表则是美国牧师约翰·麦克斯韦(John C. Maxwell)2020年出版的《成功是一种选择》(Success Is a Choice)。这些书籍都可以被看作诺曼·文森特·皮尔1952年畅销书《积极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的当代继承者。值得注意的是,皮尔主持了特朗普的第一场婚礼,并似乎塑造了这位未来总统的思维方式——至少是在他不沉溺于宇宙虚无主义的时候。皮尔所吸收的是一系列自镀金时代以来就广为流传的信仰和实践,统称为“新思想”(New Thought)。新思想声称,通过恰当的专注和祈祷,任何人都可以获取深层的神圣创造力,并将其用于解决他们面临的包括从疾病到失业的任何困难。
尽管“新思想”及其后继者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了自助出版产业,但哲学式自助的先驱也早已存在于美国文化当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阿多诺(Theodor Adorno)认为,从占星术到看手相,1940年代美国兴起的神秘主义热潮就是人们对于一个似乎无法被理性控制的社交世界的应对机制。这种世界不做回应、无法控制的感觉在战后美国面临环境危机、核灾难和1970年代经济停滞时愈演愈烈,许多与反文化和新时代运动相关的实践,如自耕生活运动、共同生活运动、迷幻药使用和自由恋爱主义等等,都可以被理解为在传统成就变得毫无意义时重新聚焦于生活中简单即时的快乐的尝试。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当代美国人似乎越来越热衷于“精神的、形而上学的和波西米亚式的”追求,用“禅宗、存在主义和垮掉的一代生活方式”等风格取代了社会变革的雄心,而这些试图在个人项目或私人精神修行中寻找意义或目标的尝试很快作为一种健康生活方式被现状所吸收。
而马尔库塞所指出的精神实验风潮催生了将自助与哲学相结合的新出版趋势。自诩为“哲学娱乐家”的艾伦·沃茨(Alan Watts)在20世纪50年代一举成名,在其畅销书中向读者介绍东亚哲学并提供实用生活建议。罗伯特·皮尔西格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1974)和本杰明·霍夫的《The Tao of Pooh》(1982)也曾凭借对“东方”和“西方”智慧的融合而登上畅销书榜单。今天的读者仍然可以在韩裔美籍禅宗僧人慧敏禅师(Haemin Sunim)的著作中找到以世俗哲学视角诠释的禅宗智慧。慧敏禅师传递着关于超脱和接纳的熟悉信息,他将帮助你培养《对不完美事物之爱》(Love for Imperfect Things,2016),并教你《当事与愿违》(When Things Don’t Go Your Way,2024)时如何应对。慧敏禅师解释道,“我们不快乐,是因为我们无法与现实和解,我们希望事情与正在发生的有所不同。”
贝克指出,这条被以不同的语体和习语表达的建议,正是自助哲学的核心,这一流派的拥护者们认为它动摇了当下文化的根本信念。奥利弗·伯克曼(Oliver Burkeman)在2024年出版的《凡人沉思录》(Meditations for Mortals)中引用德国社会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观点抨击“我们能够掌控世界的想法、希望和欲望”——据称这是“我们称之为‘现代’的那种生活方式的文化驱动力”。但在贝克看来,这种洞见远不如自助哲学家们所宣称的那样具有颠覆性,否则它就不会以各种形式存在并长期广受欢迎(且有利可图)。与其说这是主张只要用心就能做到任何事的自助流派的“解药”,不如说是它的双面神雅努斯,平静地回望我们社会曾经燃起又碾碎的全部希望。
文章接着写到,虽然近日自助哲学的早期先驱强调深奥的“东方”智慧,但近几十年来成功发展为成熟产业的却是斯多葛主义,这一从公元前三世纪在古希腊流行并在罗马帝国的最初几个世纪中持续盛行的哲学运动。古代斯多葛学派认为宇宙是理性的化身,或者说是一种类似命运的“逻各斯”(logos),并致力于揭示其原理。对于今天的斯多葛主义的拥趸们而言,如《哲学的指引:斯多葛哲学的生活之道》(How to Be a Stoic,2017)作者马西莫·匹格里奇(Massimo Pigliucci)所言,则主要将其视为“一个尽可能过上最好生活的框架”。
贝克提到了记者海蒂·奥布莱恩(Hettie O’Brien)2020年10月发表在《The Baffler》上的对于新斯多葛主义兴起( Grin and Bear It:on the rise and rise of neo-Stoicism)的评论。奥布莱恩发现,斯多葛主义在大流行期间重新受到关注,这种古老哲学从1980年代兴起,并在1990年代“历史的终结”后急剧攀升。她指出,苏联所代表的体系性替代方案的丧失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胜利,使得决定社会现实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冷酷无情。克林顿时代的很多美国人都感到受制于命运,转而向斯多葛主义寻求慰藉。比尔·克林顿本人就在1992年告诉历史学家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除了《圣经》之外,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
贝克指出,斯多葛主义变得无处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美国服饰(American Apparel)市场总监瑞安·霍利迪(Ryan Holiday)孜孜不倦的宣传。霍利迪在2014年出版的《障碍即道路》一书中(The Obstacle Is the Way: The Timeless Art of Turning Trials into Triumph)中初涉斯多葛主义,大获成功后推出了一系列续作:《自我是敌人》(Ego Is the Enemy,2016)、《沉静是关键》(Stillness Is the Key,2019)、《自律即命运》(Discipline Is Destiny,2022)等等。他还打造了一个包括一档热门博客和一个名为“每日斯多葛”的YouTube频道。批评人士尤其关注霍利迪在硅谷和一些致力于宣扬厌女或种族主义(往往两者兼有)的线上社区的粉丝。古典学者唐纳·扎克伯格(Donna Zuckerberg)曾指出男性圈的男性对斯多葛哲学有着深深的迷恋。越来越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斯多葛主义在右翼极端分子中的流行,极右翼网红、涉嫌人口贩卖的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也自诩为斯多葛主义的信徒。这与斯多葛主义本身的倾向有关:古典学家、《沉思录》译者格雷戈里·海斯(Gregory Hays)指出,斯多葛主义在坚信社会等级制度必要性的罗马精英男性中盛行。
不过,贝克认为,对斯多葛主义的当代运用通常流于平庸而非险恶,充满了令人厌倦的陈词滥调和同义反复。因此,新斯多葛学派开始推陈出新。唐纳德·罗伯逊(Donald J. Robertson)2019年出版的《像罗马皇帝一样思考》(How to Think Like a Roman Emperor)一书探讨了斯多葛主义与现代认知行为疗法原则之间的联系,去年的新书《像苏格拉底一样思考》(How to Think Like Socrates)则称这位雅典大师成为“斯多葛学派的教父”。贝克不无讽刺地写道,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因为苏格拉底可以被视为所有后续西方哲学的“教父”。而即使斯多葛主义的泡沫破裂,出版业也完全有能力将古代哲学重新包装成当代建议手册。今年一月出版的《超越斯多葛主义》(Beyond Stoicism)由多位明星斯多葛主义写手联袂推出,旨在让读者相信,即使他们不认同斯多葛主义,也能从其他古代哲学中找到慰藉,例如怀疑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作者们解释说,尽管这些哲学体系在教义上存在差异,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帮助人们应对一个动荡不安、几乎无法掌控的世界”——“这与我们自身所处的动荡时代非常相似”。哲学思考被具体化为一种应对工具,像冰淇淋口味一般,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来选择。
不过,贝克也承认整个自助哲学不能被等同于流行斯多葛主义的空洞无物。自2020年夏天以来,一些斯多葛主义复兴的倡导者也开始消化最常见的政治批评。在《不必担忧的理由:如何在混乱时代保持斯多葛主义》(Reasons Not to Worry: How to Be Stoic in Chaotic Times ,2022)一书中,澳大利亚作家布里吉德·德莱尼(Brigid Delaney)坦言,她最初开始阅读斯多葛主义哲学时也曾担心“斯多葛主义强调个性的责任,认为我们的影响范围极其渺小,这意味着社会正义和争取社会变革的行动对一个践行斯多葛主义的人来说毫无空间”。但她最终将斯多葛主义视为绝望感和沮丧感的解药,这些感受会让人更难参与政治行动。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家基兰·塞蒂亚(Kieran Setiya)在其著作《人生艰难:哲学如何帮助我们找到出路》(Life Is Hard: How Philosophy Can Help Us Find Our Way,2022)中援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塞蒂亚根据他对阿多诺的理解指出,与其问如何构建完美社会,不如认识到“迈向正义的每一步都具有价值,而一步会引领我们走向下一步”。 类似地,阿夫拉姆·阿尔珀特(Avram Alpert)在《足够好的人生》(The Good-Enough Life,2022)一书中指出,摒弃我们对“伟大”的执念,有助于我们抵制过度政治投入的诱惑,这种诱惑会让组织者精疲力竭、领导者自负自大,而这正是黑人自由运动的主要教训之一。阿尔珀特认为,曼森“别在乎”的告诫“相当不错”,但必须伴随着对结构性力量的理解,以及改变这些力量的决心。萨米尔·乔普拉(Samir Chopra)在2024年出版的《焦虑》(Anxiety)一书则敦促读者反思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如何导致我们所有人生活中都存在着无法消除的生存焦虑和痛苦。他认为,这种社会制造的焦虑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纠正的,并指出接纳、行动和反思的巧妙结合或许才是与焦虑共处的良方。
贝克在文章最后写到,他在2024年初阅读了这些书籍,他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新思想运动的历史以及它所启发的美国主流自助书籍潮流的书。当他因为加沙永无止境的种族灭绝、高等教育缓慢地走向毁灭以及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明显缺乏有效力量来抵制极右翼威权主义的现实感到绝望时,这些自助哲学书籍减轻了他的愧疚感,让他感到安心。但他在某个时刻发现,自己花了更多时间在思考自身的绝望上,而不是思考那些引发绝望的外部问题。他由此认识到,过分高估自身的重要性固然会酿成政治和心理上的灾难,但我们也可能高估自身的渺小,而这会让我们忘记自己的未竟的目标,当这些目标是阻止种族灭绝或无家可归时,放手就会酿成悲剧。很多人觉得这些目标无法企及,是因为很少有人体验过参与集体行动如何增强和扩展我们的个人能动性。当我们只能靠自己时,塑造我们生活的境况往往显得陌生而单一,迫使我们在自助的两极之间做出选择:积极思考的虚幻乐观和“哲学”所教授的斯多葛式接受。贝克指出,一些被哲学家们抨击的积极思考论调,只要我们坚持以第一人称复数视角去看问题,就是正确的。我们有责任掌控自己的人生走向;我们可以做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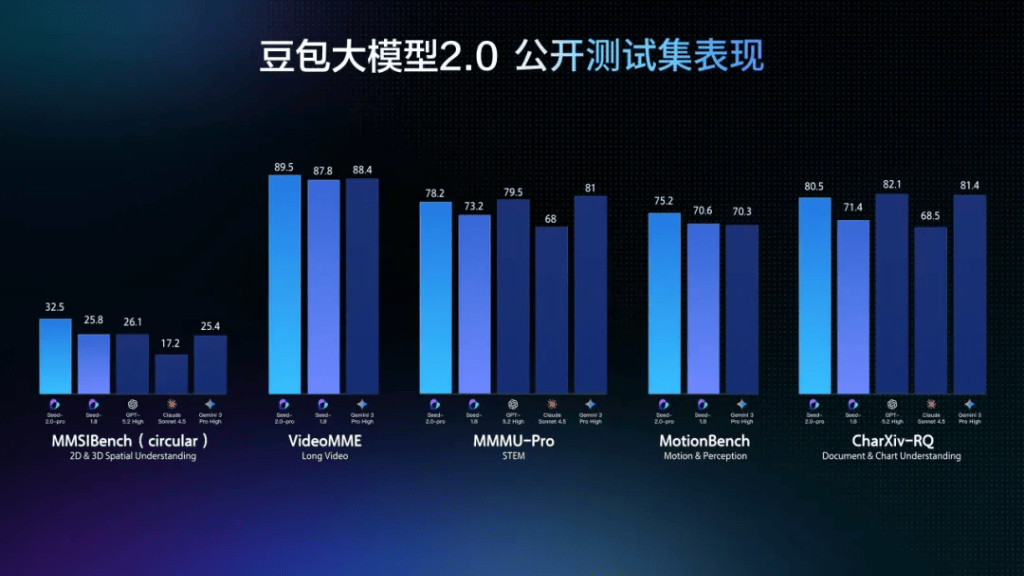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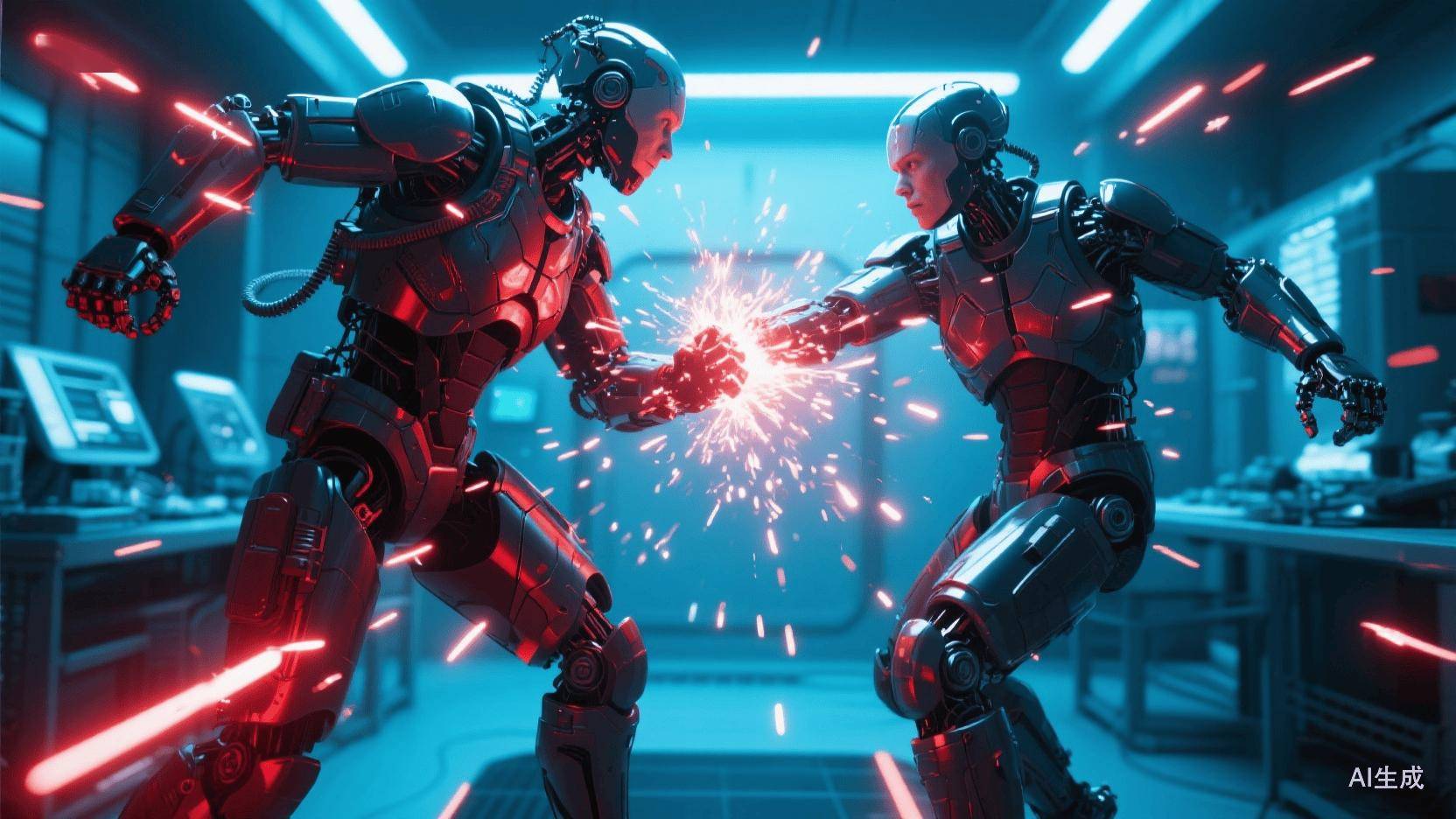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