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10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极致的星空,和想要抬头看天的人……》的报道。
浩瀚星空,无垠宇宙。
漫步其下,蓝色星球上总有人想一探宇宙奥秘。无论是跋涉万里寻觅世界级天文台址,还是为了拍摄星星“飞越全球”,或是监测日益拥挤的太空以防止卫星“堵车”,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追着心中最美的星星。
邓李才:“最能爬山”的天文学家找到世界级天文台址
柴达木盆地西北角,阿尔金山脚下,沿着215国道穿越戈壁来到冷湖石油工业遗址保护区,成片的断壁残垣映入眼帘。
而就在不远处的赛什腾山上,一个个银白色的天文圆顶密集排列——这里,正悄然成为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观测基地。
谁也想不到,冷湖这座曾因石油资源枯竭而被遗忘的小镇,竟会与星空结缘。而这背后的故事,要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李才说起。
对于天文学家来说,一台先进的天文望远镜就是他们探索宇宙的“眼睛”。然而在1989年,邓李才远赴意大利求学时却深刻感受到,中国天文学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相距甚远。在欧洲,望远镜不仅口径更大,操作技术手段也更加发达。
尽管当时互联网技术尚不发达,但邓李才的一位意大利同学已能在欧洲远程控制位于智利的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邓李才不由想起自己早前在国内的经历:有一次观测结束后突遇天气变化,望远镜圆顶需紧急关闭,但由于设备老旧,大家只能合力手摇天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合上”。
国外的学习经历让邓李才意识到,中国天文学要走向国际前沿,必须拥有先进的大型望远镜设备和观测技术。
建设大科学装置,选址是重要前提。2017年,邓李才为自己负责的“恒星观测网络计划”光学望远镜进行搬迁选址。这台望远镜原本放置在青海德令哈市,但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亮的灯光让望远镜观测受到严重影响。
就在邓李才为安置望远镜发愁时,一位地方干部也在谋划所在地区的未来。2015年,田才让调任青海冷湖,负责建设工作。当时的冷湖,人口持续流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但在一番考察之后,田才让注意到了冷湖纯净的星空。
经过朋友介绍,田才让找到了邓李才的办公室。当时,路过车辆扬起的尘土会对望远镜观测造成影响。见面之前,邓李才刚给观测站附近的固沙植物浇完水。田才让看着身穿带泥点的工作服、满是尘土的徒步鞋的邓李才,心里直打鼓:“这真的是国家天文台的专家吗?不会是找错人了吧?”
尽管如此,田才让还是开门见山:“冷湖的星空条件很好,我们想请你去考察能否建天文台。”
有了之前德令哈的经历,邓李才不太客气:“我们把望远镜放在冷湖,你们能做到长期保护吗?”
田才让立即做了一番“功课”。“他一个星期后就拿着红头文件来了。”邓李才说,看到地方政府保护暗夜星空、支持天文观测发展的承诺,他被打动了。
天文观测对环境要求十分严苛,一流天文台址往往需要符合云量小、空气干燥、大气稀薄、视宁度好等条件。根据历史选址资料,邓李才初步判断,冷湖基础条件不错,唯一让人担心的是风沙。这里究竟是否适合建望远镜?得先找到不受风沙影响的地方。
邓李才用遥感数据筛了一遍,最终锁定赛什腾山。“它从戈壁中拔地而起,相对高差大,能避开底层沙尘,也是冷湖附近仅有的一座高山。”他说。
2017年10月,邓李才带着团队第一次抵达山脚下。
那是个晴朗的夜晚,他没靠专业设备,只用手机就拍到了银河拱门。在智利、美国夏威夷、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邓李才曾见过多个世界顶级台址的星空。而站在赛什腾山下的那一刻,他心跳加快了,“从感官上说,冷湖的星空不输给它们。”
赛什腾,蒙古语意为黑色不长草的山,山峰陡峭、碎石遍布,最高处海拔超4500米。此前从未有人为天文观测登顶此山。
邓李才和田才让拿着地形图、拄着登山杖,沿着山脊和沟壑向上爬。一边探路,一边用喷漆做标记。
“山上根本没有路,有一次我在攀爬中脚下突然踩空,幸亏马上用手抓住岩壁,控制住了身体。”邓李才说,团队中的年轻人杨帆体重较大,爬山时格外吃力,每次上山会带一瓶可乐,“登顶后喝可乐,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当时,邓李才了解到,国家考虑建设一台超大口径光学望远镜项目,但备选台址的条件都不理想。“如果我们不快点拿出冷湖的选址数据,可能就要错过这个机遇。”
缺氧、头痛、体力透支……回忆当初爬山的日子,邓李才从未想过放弃:“比起上世纪欧美人在智利安第斯山脉骑着毛驴选址,我们开着越野车,后来甚至用上了直升机,已经幸福多了。”
2018年,在当地政府部门支持下,邓李才团队用直升机吊装选址设备。其中最关键的是一台视宁度测量仪,要在山顶完成基建和配套设备建设。当天晚上,邓李才下山准备第二天的运输任务,杨帆主动选择留下:“设备调试好了,我先测一夜看看。”
看到屏幕中不断跳出的数据,杨帆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杨帆跑出帐篷到处找信号,终于拨通了邓李才的手机:“数据大超预期,视宁度0.79角秒,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邓李才(左三)和团队在冷湖赛什腾山进行选址工作。(受访者供图)
邓李才握着手机,一时在原地呆住了——这里,就是一直寻寻觅觅的地方!
2021年,邓李才研究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冷湖赛什腾山光学天文台址勘选结果,正式确认冷湖赛什腾山为国际顶级光学天文台址。国内天文学界为之一振——一直以来,全球最好的光学天文台址都集中在西半球,如今中国也有了自己的一流台址。
鸭舌帽、徒步鞋,外加一件冲锋衣,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上快走也不喘气——初次见到邓李才,你很难相信他已年过花甲。受家人影响,他高中接触冬泳,在意大利留学时常去登山徒步,现在爱打羽毛球。
2009年开始,因工作需要,邓李才频繁往返高原。一次体检中,他发现自己的血压明显升高。“医生说这可能和频繁进出高海拔地区有关,建议服药控制。”他回忆道。
半年过去,他依靠药物维持血压稳定,也在思考更根本的解决方式:能不能通过增强自身机能来适应这样的工作方式?他开始制定严格的锻炼计划:坚持跑步、健走,加强心肺功能,同时控制体重。一段时间后,他逐渐减少药量,最终成功停药。
如今邓李才仍坚持锻炼、控制饮食。“没有好的体能基础,冷湖选址可能还真做不下来。”他说。
冷湖选址的成功,锻炼出了一支经验丰富的选址团队。邓李才坦言,自己到了这个岁数,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更大突破越来越难,但还能为其他人铺路。
大型天文台的选址是一项耗时漫长的系统工程,若让处于科研黄金期的年轻学者全力投入,可能不利于个人职业发展。也正因如此,邓李才觉得,像自己这样的过来人多承担一些基础性、支撑性的工作,既是一种责任,也有利于人才队伍建设。
如今,在冷湖天文观测研究基地,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望远镜或已投入观测,或正加速建设,这里逐渐成为亚洲最大光学天文观测基地。邓李才最喜欢傍晚时分站在山上,看望远镜圆顶依次打开,望向深空。
天文学从来都不遥远。它只需要一片极致的暗夜星空,和一群想要抬头看天的人。
王凯翔:“星空选中了我,让我替它发出一点点光”
5个月前,阿尔卑斯山的冰川险峰间,一架直升机在强风中不停摇摆。机舱内,王凯翔有些紧张,脑海里闪过的念头却是:“我还有不少科研成果没发表呢。”
几天后,在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勃朗峰的登山滑雪中,他在登顶下撤时又经历了一次意外滑坠。“如果不是当时有结组,那我大概率将坠下千米深的山谷……”
当天傍晚,他背着滑雪板疲惫不堪地走在森林里,转身望去,滑行过的破碎冰川和远处夕阳余晖中的小镇美得不可言喻。极致的险和极致的美在此刻交织,这种矛盾统一的体验,让他痴迷不已。
但对王凯翔而言,比群山更高远的召唤来自星空。
夜幕垂落,星光闪烁。头顶是遥远的光点,也是他自少年时代起便深深着迷的宇宙。
2009年7月22日,一场罕见的日全食掠过长江流域,那时还在上初中的王凯翔,和上万人一起聚集在浙江绍兴的广场上,目睹了“太阳被月亮吞没”的震撼瞬间。
“光迅速暗下去,月球阴影快速地压过来,全场惊呼尖叫……”他举起手中的卡片相机,拍下了人生第一张天文影像。尽管粗糙,却真实记录了他与宇宙奇观的第一次正式“相遇”。
“那种超越现实的体验,会长久地在心中泛起波澜。”
从那以后,他主动阅读天文书籍、尝试观测天象,本科阶段起深入接触严谨的天体物理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多彩的星空摄影世界。他说,天文学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学科,而拍摄星星,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科学的延伸”。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项爱好会在许多年后,变成支撑他走过科研低谷的力量。

这是澳大利亚十二使徒岩上空的星河。(受访者供图)
博士阶段,王凯翔进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系,主攻星系演化研究。他形容自己做科研就如同“福尔摩斯探案”,或像是“宇宙考古”——
“我们看到的星光,可能是上百亿年前发出的,我的工作就是解码这些光里的信息,拼凑出星系演化的故事。”
可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研究的关键期,新冠疫情袭来,导师的线下指导中断了3年,他成了学术路上的“孤勇者”。
面对延迟毕业的压力、外界的质疑,他找到了独特的解压方式——进山滑雪、拍摄星空。
“极限运动给了我内心的支点,让我知道即使科研遇到挫折,我还能做个快乐的滑雪教练。而星空摄影训练了我的观察力,让我在复杂数据中更快捕捉关键信息。”这些看似与科研无关的爱好,最终都成了支撑他前行的力量。

这是王凯翔参加2023年UTMB环勃朗峰越野赛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2023年,在西雅图举办的美国天文学会(AAS)新闻发布会前,王凯翔把自己关在酒店房间里哭了一场。“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终于能把研究多年的成果拿出来,那种紧张又珍视的心情,就像要把藏了很久的宝贝展示给全世界看。”
2023年,他以独立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身份在《自然》期刊发表论文,首次系统揭示超致密矮星系由普通矮星系演化而成的完整机制。一位业内专家专门发来邮件:“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文章里的那幅图,真的很cool(酷)。”
王凯翔总说,天文学研究常要“靠天吃饭”,这份不确定性恰好与星空摄影奇妙契合。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一次观测,是在夏威夷莫纳克亚天文台。“那里的凯克望远镜是全球最顶尖的设备之一,我们好不容易申请到3个夜晚进行观测。”
可当他跨越太平洋抵达夏威夷,连续多日的暴风雪天气却让观测计划全部泡汤。原定要和哥伦比亚中学生连线直播观测实况,最后只能换成讲报告分享。
“但我大概是第一个在那座天文台上滑雪的中国研究者。”王凯翔笑着说,“没观测成功,却收获了别样的体验。”
类似的“意外”,也发生在星空摄影的途中。他曾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等待英仙座流星雨,却遇上从撒哈拉沙漠袭来的沙尘,整片天空灰黄模糊,几乎无法拍摄。那晚,他把相机架在一旁自动拍摄,铺了垫子躺在半山腰,安静地看着朦胧的天幕。
“那次没拍到出彩的作品,但那个夜晚依然属于我。在星空下,我的想象力是不受束缚的。那是一种极致的自由。”
正是这些“不成功”“没拍到”,让他渐渐懂得“等待”的意义——科研没有绝对的成功或失败,摄影也不必有“必须出片”的压力,顺应自然节奏,反而能收获惊喜。
2024年5月,剧烈的太阳风暴来袭,通过空间天气预报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判断,王凯翔提前锁定北京以北的金山岭—蟠龙山长城一带,认为可能出现极光。地磁暴开始的当晚,他与同伴驱车前往,经历一晚的风雨和沙尘,为了寻找晴空区,在寒风中等待了几个小时。
当弥散的红色光柱出现在长城背后的天际时,他忍不住落下眼泪。“那是第一次有人在北京境内的长城上拍到极光。我们记录下了画面,仿佛参与了一场创造历史的事件。”
在王凯翔眼中,星空摄影是一种与宇宙对话的方式。而这种“对话感”,与科研中发现新天体的体验如出一辙。
一次分析观测数据时,他偶然瞥见一个从未被记载过的天体,忍不住在心里默念:“嘿,亿万光年外的小家伙,这是第一次有地球人注意到你吧?”那种雀跃,就像解开了一道藏了很久的谜题,是任何荣誉都替代不了的体验。
“每当这时总会觉得,不是我主动选择记录星空,而是星空选中了我,让我替它发出一点点光。”
凝视宇宙,给他带来了什么?
“它让我变得更简单。”王凯翔说,“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下,人类的烦恼渺小得不值一提。万物终将消失,反而让人更珍惜当下所能感受到的一切——一朵花,一块岩石,一条冰川,一片海洋,大到整个地球、太阳,都不是永远存在的。”
“如果大家都能多看看星空,或许会发现,世界其实没那么复杂,而探索与热爱,永远值得我们全力以赴。”他说。
刘博洋:用热爱链接大众与星空
刘博洋的天文梦始于童年,长大后这颗热爱的种子不断生根发芽:他是大学天文系里组织社团、带同龄人观星的组织者;是网络上花数小时查资料,第一时间解读重大天文发现的科普者;更是如今建起监测网,观察太空的“守护者”。
从“一个人看星星”到“带一群人看星星”,再到守望太空,刘博洋把小众的天文领域,变成了大众能触摸、能听懂的浪漫。
1990年,刘博洋出生在内蒙古。小时候,父母带他去北京参观多家博物馆,唯独天文馆让他流连忘返。父母托人购买的一台入门望远镜,为刘博洋打开了通往星空的第一扇窗。
通过这台望远镜,刘博洋第一次清晰看到月球表面的环形山,那些坑洼不平的阴影在他心中种下了对宇宙的好奇种子。
2005年,刚上高中的刘博洋加入学校天文社,却没想到这个决定会改写他的人生轨迹。
“那时候我对天文的了解,仅限于用家里望远镜看到的太阳和月亮。”刘博洋说,一次社团活动中,学长学姐组织大家去郊外观测,当20厘米口径望远镜对准银河时,他第一次看到“银河中如丝绒般的群星”,那种震撼让他记忆犹新。
在社团成员介绍的天文论坛网站中,刘博洋常通宵浏览帖子恶补知识。仿佛新世界的大门向他敞开,他才知道原来全国有这么多天文爱好者,有人在拍深空,有人在手磨主镜,还有人会分享自己发现的小行星。这让他第一次觉得,天文不是一个人的事。
高中毕业时,作为呼和浩特市天文爱好者协会的成员,刘博洋受邀去香港交流。在香港,天文爱好者当时正从胶片天文摄影转向数码摄影,他第一次上手口径达半米的天文望远镜。“大开眼界之后,我逐渐认为,天文知识的传承离不开平台和引路人。”刘博洋说。
这种想法,在刘博洋进入北京大学天文系后转变为具体行动。作为北大青年天文学会成员,他发现很多偏远地区的高校没有天文社团,就算有,也缺设备、缺指导,学生只能自己摸索。
于是刘博洋牵头成立“北京高校天文社团联盟”,又发起全国天文社团发展论坛。他觉得,天文是一个小众领域,他希望让同样喜欢天文的同龄人找到组织,就像当年学长带他看银河,他也想成为那个“递望远镜”的人。
2012年,刘博洋成为了一名知乎答主,为网友科普天文知识。为了解答网友“脑洞大开”的问题,他经常花数小时查前沿英文资料,有时一篇文章要打磨一个月。天文领域有新发现时,他会第一时间呈现通俗易懂的解读。
本科毕业后,怀揣对天文的热爱,刘博洋选择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深造,之后又转学前往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继续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
读博期间,刘博洋一度陷入迷茫,看着身边优秀的同龄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适合走科研这条路。当时,他在知乎平台上有了10万粉丝,通过数篇“火出圈”的天文科普文章,在天文圈已经小有名气。

2018年,刘博洋在参观默奇森射电天文台(MRO)的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受访者供图)
临近毕业,导师对刘博洋说,你可以不做科研,但如果不做科普,一定是科普界的一大损失。这句话点醒了他——为什么不结合自己的优势,为更多人解读宇宙的奥秘?
刘博洋渐渐发现,相比做科研,自己更擅长把复杂知识讲明白,而在国内,专业的天文科普作者恰恰是稀缺的。而随着自媒体平台快速发展,当时一些鼓吹外星人、“UFO崇拜”等邪说的伪科学大行其道。
2019年,刘博洋发现一个传播力甚强的邪说团体,打着“外星文明”的旗号,诱导人相信“自己是外星人”,甚至有家长联系他说自己的孩子在接触这个邪说后精神异常,被迫休学2年治疗。
“我一开始也想过,这种‘怪力乱神’值得花时间回应吗?”
可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受到心理创伤,刘博洋觉得这种邪说需要专业科普来进行对抗。
那段时间,他翻遍了这类团体从起源到发展壮大的资料,梳理出他们编造故事的套路,又结合专业知识,逐一反驳“飞碟学”“宇宙人类”等概念,文章发表后很快得到广泛传播。
不久后,一些伪科学账号因“担心被追究”,悄悄改了名,停止了运营。刘博洋说:“那时候我才明白,科普不只是讲知识,还能‘救人’,这种价值,比发一篇科研论文更让我有成就感。”
做科普久了,刘博洋慢慢有了困惑:光靠自己查资料、写文章、拍视频,总觉得离“真正的天文一线”有点远。他直言,完全靠求学期间积累的知识做科普,时间长了难免“江郎才尽”。
也是这份顾虑,让他最近把职业重心转向了创业。不是放弃科普,而是想离科研和科技产业更近一些。“借时代东风,通过科研界和产业界的力量提升自己,以后再科普,才能有更多的一手信息。”刘博洋说。而他找到的新方向,恰好是“从仰望星空到守护太空”。
现在我们抬头看星空,除了星星,还会看到不少“会动的光点”,这些大多是人造卫星,而且数量正快速增长。
“以前的星空是‘静态’的,星星在哪几乎不变。现在不一样了,天上多了好多人造卫星,以后会更多。”刘博洋说,就像马路上的车多了会堵车,天上的卫星多了也一样,所以人类要想持续利用太空,就得知道每颗卫星在哪儿,有没有和其他卫星碰撞的风险。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得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这正是他创业项目的核心目标。
2022年,刘博洋成功记录了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全部12种构型,为中国航天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2023年,有了知乎“灯塔计划”的100万元支持,刘博洋团队把这套跟踪空间站的技术发展成布局全国的监测网,给太空装了一套“监控系统”。
刘博洋给这套系统起了个接地气的内部代号——“天罗地网”。通俗地说,就是在不同地方建观测点,盯着天上的卫星和各种“太空目标”,记录它们的位置、轨迹,并连成一张监测网。
这张网刚建成没多久,就实实在在帮了个大忙。2024年,某卫星发射异常出现紧急状态后,刘博洋团队接到要求投入支援,在发射后仅5小时便获取了卫星与火箭上面级已完成分离的影像,协助任务方以更高时效判定卫星状态,为后续救援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而这一切,还是离不开刘博洋做科普的初心——现在团队拍的卫星分离画面、算的轨道数据,都是最鲜活的科普素材;以后大家再听到“太空‘堵’卫星怎么办”“怎么防小行星撞地球”,不再只能面对抽象的文字,而是能看到他们呈现的解决方案。
在刘博洋眼中,自己或许不是一个出色的天文学家,却是最愿意和大众一同领略星空的人,而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用影像直观呈现自己实现某个科学目标的过程,是在“大航天时代”做科普不可或缺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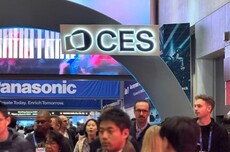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