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整理:Web3天空之城
[城主说] 作为20世纪物理学的泰坦,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博士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他的杨-米尔斯理论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粒子物理学的走向。然而,杨振宁的传奇远不止于公式和理论。他是一座桥梁,连接着战火纷飞的旧中国与科技鼎盛的新世界,连接着物理学的黄金时代与数学的前沿疆域,也连接着东方强调纪律与西方崇尚自由的两种教育哲学。
这一场深度对话是2009年杨振宁在所长期任教的石溪大学做的大师访谈,杨振宁回顾了他波澜壮阔的求学和研究经历。从昆明西南联大的求学岁月,到乘坐运兵船远渡重洋;从与费米、奥本海默、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的近距离交往,到在石溪大学意外点燃物理与数学两大领域的融合之火。这访谈也揭示了这位科学巨擘眼中,驱动物理学发展的“结构之美”,以及他对塑造未来创新人才的深刻洞见。
核心观点摘要
“一切事物的结构往往蕴藏着隐藏的美。如果你能隐约感受到其中的一些美,就不要放手。……1954年米尔斯和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它与实验不符,没有人相信我们。但我们看到了结构的优美之处,所以我们把它写了下来。”
“费米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当他对某事进行推测时,你知道那是基于他已经思考过的具体想法。因此,他的话语带有权威性,因为你知道这些不是随意的或信口开河的言论。”
“随着这个纤维丛理论的发展,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如果你想问这种结合是如何发生的,我会说这与我和吉姆(西蒙斯)以及那本词典中的空白之处和石溪大学有关。”
“中国的体制更擅长培养大量会成熟的人……但美国的体制更加自由,……看看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创造数万亿美元的价值……这种创新精神,这种自由精神,正是美国教育体系和社会所擅长培养的东西。”
“这在我的人生中非常重要,即了解我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
“我总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聪明的孩子,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她在中国的重点高中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中国的大学接受教育,并在美国接受良好的研究生教育。我自己就从中受益匪浅。”
与巨匠同行:费米、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的印记
杨振宁的学术生涯,恰逢20世纪物理学的黄金时代。他在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历,使他得以近距离地与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头脑们交流甚至共事。这些交往不仅塑造了他的学术路径,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生动的科学群像。
谈及他的博士导师恩里科·费米,杨振宁的描述充满了敬意与亲切。费米是最后一位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都做出顶尖贡献的物理学巨匠。“我说过费米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杨振宁回忆道,“他非常可靠。……当他对某事进行推测时,你知道那是基于他已经思考过的具体想法。因此,他的话语带有权威性,因为你知道这些不是随意的或信口开河的言论。” 这种严谨务实的学风深深影响了杨振宁,两人不仅在学术上合作发表了至今仍被引用的论文,在生活中也因费米家中的“方块舞派对”而关系融洽。
而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17年,是他学术生涯的巅峰期,这段时期由另一位传奇人物——罗伯特·奥本海默所主导。奥本海默作为研究院的院长,为学者们创造了一个可以免受行政俗务干扰的“象牙塔”。杨振宁正是在这里,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工作。他甚至透露,奥本海默曾属意他接任院长一职,但他最终以“不是行政型的人”为由婉拒,并选择了当时尚在起步阶段的石溪大学,开启了另一段传奇。
对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杨振宁则怀着一种晚辈对前辈的敬畏。当他1949年到达研究院时,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但两人仍有交集。杨振宁回忆起一次被爱因斯坦邀请讨论论文的经历,“他的气场让我感到非常敬畏。我从那次谈话中没得到太多收获。” 在他看来,爱因斯坦深受经典物理学传统的熏陶,并以此为基础,“在20世纪为物理学发起了两次半的革命”——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以及他作为重要贡献者之一的量子力学。
杨-米尔斯理论的诞生:对“结构之美”的坚持
1954年,杨振宁与罗伯特·米尔斯合作发表了杨-米尔斯理论,它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数学框架来描述除引力外的另外三种基本力(电磁力、强核力、弱核力),即“规范场论”。这一理论如今已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核心,但在当时,它却是一个与实验数据相悖、无人相信的“异端邪说”。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坚持这个看似错误的想法?杨振宁给出的答案,充满了哲学意味:对数学结构内在之美的信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它如此重要,但我们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而且数学结构非常优雅。所以我们发表了一篇关于它的论文。” 他常常告诫学生:“一切事物的结构往往蕴藏着隐藏的美。如果你你能隐约感受到其中的一些美,就不要放手。”
正是这种对“优雅”和“美”的执着,让他们没有因为眼前的实验不符而放弃一个具有深远潜力的理论框架。二十年后,实验终于追赶上了理论的脚步,杨-米尔斯理论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彻底改变了物理学。
物理与数学的意外交融:石溪大学的“词典”故事
杨振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学术领袖。他在石溪大学执掌理论物理研究所的33年,不仅将其打造成世界级的学术中心,还意外地促成了现代物理学与数学的一次历史性融合。
故事始于一次授课中的灵光一现。杨振宁在黑板上书写广义相对论的公式时,突然意识到其结构与杨-米尔斯理论惊人地相似。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他求助于当时石溪大学年轻的数学系主任、日后成为传奇投资人和慈善家的吉姆·西蒙斯。“我说,吉姆,……你看,它们非常相似。他思考了一会儿。他说,是的,这并不奇怪。它们都是纤维丛。所以,我说,什么是纤维丛?”
这次交流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在物理学家们看来艰涩难懂的数学概念“纤维丛”,经由西蒙斯的一系列通俗讲解,揭示了其与规范场论的深刻联系。为了系统化这种联系,杨振宁与吴大猷合作撰写了一篇论文,创建了一本物理学与数学术语的“小词典”。有趣的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源”(Source),在数学中却没有对应词。“我们把它留空了,” 杨振宁笑着说。
正是这个“空白之处”,激发了来访的数学家辛格和阿蒂亚的兴趣,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数学家从未触及过的有趣概念。“这现在成为了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他们称它为唐纳森理论。” 杨振宁总结道:“在20世纪上半叶,物理学和数学是分离的。……但随着这个纤维丛理论的发展,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又重新走到了一起。所以,如果你想问这种结合是如何发生的,我会说这与我和吉姆以及那本词典中的空白之处和石溪大学有关。”
东西方教育之思辨:纪律与自由的平衡
凭借其横跨中美的独特经历,杨振宁对两国教育体系的优劣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两种体系的根本差异源于不同的社会哲学,各有其利弊。
中国教育的优势在于纪律和严格的基础训练。“在中国,如果你有一个8岁的孩子,跟他说你应该做作业,他或她就会去做作业,” 他观察到,“在这里,他或 she 会说,我不想做。……做作业可能会很枯燥,这个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这种训练使得中国学生在基础知识上极为扎实,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初到芝加哥时,发现在中国的所学甚至比美国顶尖大学的课程更深入。
然而,这种体系的弊端也同样明显。“他们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制度不好。所有的孩子都训练过度。……他们有变得像机器人的倾向。他们不为自己思考。”
相比之下,美国教育体系的优势在于它鼓励自由探索和创新精神。学生们不被束缚,有更多的空间去发现和追随自己的兴趣。“看看比尔·盖茨,” 杨振宁举例说,“他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创造数万亿美元的价值……这种创新精神,这种自由精神,正是美国教育体系和社会所擅长培养的东西。” 当然,其代价是许多学生在基础训练上有所欠缺,人生目标也相对模糊。
他认为,两种体系并非孰优孰劣,而应相互借鉴,寻求平衡。中国应“放轻松”,给予学生更多自由;而美国则需要确保那些对科学真正感兴趣的学生,能获得进入该领域所需的严格训练。对他个人而言,正是得益于两种教育的结合——在中国的扎实本科教育和在美国的创造性研究生训练——才成就了其辉煌的学术生涯。
在访谈的最后,当被问及如何感知科学中的“美”时,杨振宁的回答再次回归到了教育的本质:“允许自己对很多事情感兴趣,……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能够抓住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并充分发展它,这可能就是他或她发现某些事物优雅、美丽和有用的方式。” 这或许正是这位科学巨匠一生追求的缩影——在严格的逻辑结构中,寻找自由而优雅的美。
天空之城全文整理版 早年岁月与赴美求学
主持人: 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于1957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在他对该领域的众多贡献中,他与罗伯特·米尔斯合作的成果是杨-米尔斯理论,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他与他所在领域的其他伟大人物,爱因斯坦和费米,奥本海默和泰勒,有过交集。在石溪大学,他执导了33年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杨博士,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
杨振宁: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主持人: 您在中国长大,是一位数学教授的儿子。是的。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的早年生活吗?
杨振宁: 我出生在中国中部,但在北京长大。所以我的小学和四年的高中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在1937年,我15岁。中日战争爆发了,我的家人搬到了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叫昆明的城市,那里以滇缅公路的终点而闻名。我在那里上了大学。
1945年,我23岁。我获得了一项奖学金来到美国。所以我来到了纽约市,抵达日期是11月24日。因为在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商业交通。而我从中国西南部的昆明到美国的唯一途径,是飞往印度加尔各答。在那里我等候一艘船,一艘轮船,一艘美国军队的运兵船,这些船只被用来将中国-缅甸-印度战区超过一百万的美国士兵从那个地区运送到美国。所以我在加尔各答等了两个月,才在一个运兵船上找到一个铺位。
这艘船大约5000吨。我们穿过地中海和大西洋,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场风暴。我记得我吐得很厉害。我对自己说,也许这次旅行不值得。但无论如何,我到达了纽约,去了芝加哥,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那是一次相当冒险的经历。是的,的确如此。
当然,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来到美国,我不会说是震惊,但它确实需要一些调整。
主持人: 是你的物理学知识让你跨越了这种鸿沟吗?
杨振宁: 是的,我在昆明的大学里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后来又在同一所大学读了两年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我在中国的教育水平非常先进。像量子力学这样的东西,我在中国已经彻底研究过了。所以当我到达芝加哥大学时,那时的芝加哥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物理系,我发现芝加哥提供的量子力学课程并不像我学得那么深入,也不像我在中国上的课程那么详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我在1948年在芝加哥获得了博士学位。
原子弹的影响
主持人: 我在想,当你前往美国的时候,大约是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时候。是的。这对你在你的领域和作为一个人有什么影响吗?
杨振宁: 哦,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你知道,中国从1937年到1945年一直在抵抗日本的入侵,长达8年。那时中国非常虚弱,那是一段悲惨的时期。而且日本人非常残暴。你可能听说过南京大屠杀。是的。
没人知道美国正在研制这种新武器。事实上,据我所知,美国的大部分人也都不知道这件事。对。所以在8月的那个早晨,当炸弹被投放,当广播宣布这个消息时,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喜悦,因为每个人都知道,8年战争的苦难终于结束了。我记得我走出我们租住的房子,走到街上,突然看到很多人在燃放鞭炮。你知道,按照中国的习俗,如果你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你就会放成百上千的鞭炮。然后我拿到了一份报纸,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当然,这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大事,但我想说,美国人民在战争期间遭受的苦难不如中国人民多。因此,在中国感受到的幸福和兴高采烈的情绪也成比例地更高。
主持人: 你当时了解原子弹的物理学影响吗?
杨振宁: 通过中子碰撞可以产生巨大能量的一般物理原理,早在1938年和1939年就已为人所知。事实上,这甚至进入了教科书。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详细步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过程。你可能知道,它非常困难,以至于德国人在大约1944年或43年决定在战争期间无法完成。所以他们放弃了那个项目。幸运的是,他们这样做了。在美国,它最初被重视是因为爱因斯坦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美国政府和物理学家尤其担心德国人可能先得到它。
主持人: 所以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杨振宁: 这当然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件,不仅对20世纪而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与巨匠同行
主持人: 我当然不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于炸弹,但巧合的是你去了芝加哥,这所大学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我相信,你在那里的导师之一是费米?是的。请跟我说说费米。
杨振宁: 恩里科·费米于1901年出生于意大利。那时,意大利的物理学水平并不高。他是一位早熟的年轻人,他独自一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将意大利物理学水平提升到了世界标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说过费米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主持人: 怎么说?
杨振宁: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非常可靠。他看起来像个可靠的人,而且他的确如此。当他对某事进行推测时,你知道那是基于他已经思考过的具体想法。因此,他的话语带有权威性,因为你知道这些不是随意的或信口开河的言论。
他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实验家。你知道,在早期的世纪里,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既是理论家又是实验家。但到了20世纪,理论物理学变得非常复杂,实验物理学也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很少有人能同时做这两方面的工作。恩里科·费米是最后一位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都做出了顶尖贡献的伟大物理学家。
主持人: 你和他的关系如何?
杨振宁: 哦,非常接近了。你知道,当我到达芝加哥后,很快地,所有人都发现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训练有素。
观众1: 所以我和费米关系非常亲密和融洽。费米夫人,费米夫妇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那个,内拉,是上大学的年纪。
杨振宁: 所以费米夫妇总是在他们家举办方块舞派对,我去过很多次,非常了解他们一家。后来,在1949年,费米和我一起写了一篇论文。它叫做《我们的介子基本粒子》。我很高兴看到这篇论文至今仍被引用,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发表论文说被称为π介子的东西可能是核子与反核子的束缚态。这些可能都是太专业术语了,但总之,我们一起写了一篇论文。所以我是费米在芝加哥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你,当然,认识奥本海默。
主持人: 你和奥本海默一起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的。告诉我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观众: 众所周知,奥本海默因为他在战争期间指导原子弹项目而变得非常有名。
杨振宁: 1947年,他接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职位。1949年,他来到芝加哥,就物理学的一个新进展——重整化——发表演讲。我不会解释那是什么。但无论如何,那是当时最热门的话题。所以我被他的演讲深深吸引。我知道从那年秋天,也就是1949年秋天开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会有许多重整化方面的专家。所以我申请成为普林斯顿的博士后。奥本海默接受了我。
所以从1949年秋天开始,我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我原本只想在那里做一年的博士后,然后回到芝加哥。但我留了下来。总之,我在普林斯顿待了17年,从1949年到1966年。正如您所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名副其实的著名象牙塔。他们的学者不受委员会工作打扰,也不受研究生打扰,从而可以进行研究。事实上,我充分利用了这一点。那段时间,那17年,是我做研究工作最好的时期。
主持人: 我了解到奥本海默曾试图说服您在他离开研究所时接替他,但您却来到了当时刚刚起步的石溪大学。那里发生了什么?
杨振宁: 是的,发生的事情如下。1965年,首先,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前,他提名奥本海默为下一届恩里科·费米奖得主。恩里科·费米奖是一项总统奖。最初是颁给费米的,因为费米当时病危,他们迅速设立了这个奖项,并在他1954年去世前颁给了他。之后,许多为美国做出贡献的杰出人士战时科学工作获得了该奖项,包括贝特、泰勒等。并且可能,或者很可能,因为肯尼迪总统想要消除美国在1954年奥本海默听证会上给予奥本海默的悲痛。所以他决定在1962年将下一个奖项颁给奥本海默。但在那件事发生之前,他遇刺了。肯尼迪遇刺了。然后约翰逊成为了总统,事实上,有传言说许多反对奥本海默的人试图说服约翰逊不要颁发这个奖项。但约翰逊没有听他们的,所以举行了一个仪式,奥本海默确实赢得了该奖项。所以那是,我想是1963年或64年。但无论如何,那是在当时,所以在1965年,奥本海默刚刚经历了美国政府基本上隐晦地说,我们很抱歉,我们道歉的重大事件。
现在,奥本海默作为研究所的主任,与研究所里的数学家们相处得很困难。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就不打扰你讲细节了。他是主任,但数学组,那是当时研究所里最强大的,直到今天仍然是,他们对他很不满意。我认为,他们指责奥本海默不偏爱数学是错误的。但无论如何,他们让奥本海默在很多年里生活得很艰难。
所以,在1965年的某一天,我记得奥本海默顺道来我的办公室,说,弗兰克,我正在考虑辞去主任的职务。你怎么看这件事?我很惊讶,但我考虑了几分钟,我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决定。因为,我说,你已经在研究所工作很久了,现在是合适的时机。因为,A,数学家们反对你的力量是有规律的,在大辩论的热潮中,你很难说,我想退休。而且其次,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向你道歉了。这是正确的时机。所以,他感谢了我的意见。然后他说,我想推荐你作为我的继任者。
我的本能反应立刻是我不想做,因为我不是行政型的人。所以,我告诉他,我很荣幸你这样想,但我会考虑几天。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最终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虽然我不确定我是否会成为一个好主任,但我非常确定我不会享受当主任的生活。所以,那是故事的那部分结束。
但就在那段时间左右,比我最终决定早一点,但在他向我提出他的提议之后,刚刚被提名为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所长的约翰·托来拜访我,并邀请我加入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将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发展成一所伟大的研究型大学。所以,当我给奥本海默写那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和我的家人决定搬到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那是1965年。
主持人: 你来这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个承诺,即要在这里建立一个伟大的研究机构,因为当时这里还没有。
杨振宁: 是的。当然,你知道斯托纳书店大约在50年前开始,但它位于另一个校区。真正的扩张是从它搬到这里开始的。伟大的扩张始于约翰·托在1965年和1966年到来之后。那是一个伟大的扩张时期。我认为你今天看到的一切,在很多方面,都源于约翰·托和他的管理团队最初采取的几个步骤。
主持人: 你也帮助了他。是的,在某些方面。你也认识爱因斯坦。是的。
杨振宁: 正如我告诉你的,我于1949年去了研究所。他当时70岁,刚退休。但他住在研究所附近,所以他仍然每天步行去研究所。他不开车。他会步行到他的办公室,待几个小时,然后再走回去。当时,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界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曾多次说过,牛顿和爱因斯坦是史上最伟大的两位物理学家。但当时,他已经不再研究我们年轻人感兴趣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不太去打扰他。
然而,我确实听过他两次讲座。1951年,我想,我记得是1951年或者1952年,他派他的助手布鲁尔·考夫曼来找我,说,你刚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气体,液体,气体如何在冷却时变成液体的论文。爱因斯坦教授想和你谈谈那篇论文。所以我去找了他,我们肯定一起待了一个半小时。他的气场让我感到非常敬畏。我从那次谈话中没得到太多收获。我只记得,他反复画了一条曲线,这条曲线因19世纪的伟大物理学家麦克斯韦而闻名。
事实上,爱因斯坦深受旧物理学,即经典物理学的传统影响。统计物理学和电动力学是其中的两个分支,也是他的强项。他利用这种传统,利用他对这两个领域的深刻理解,在20世纪为物理学发起了两次半的革命。
主持人: 两次半?是的。哪一次是半次?
杨振宁: 量子力学。这三次革命通常被认为是继牛顿之后物理学上最伟大的革命。它们是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基本上是他独自发明的。
主持人: 量子力学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所以我认为那是爱因斯坦半个革命。我无法探究物理学的深度或攀登物理学的高度,无论哪个是正确的,但我想知道您是否能向我们这些非物理学家解释一下杨-米尔斯理论。
杨-米尔斯理论的诞生
杨振宁: 你知道基础物理学是关于什么的,就是询问物质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在19世纪,人们终于意识到一切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构成的。在20世纪,我们了解到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由质子、电子和中子构成的。但是质子和中子是由什么构成的呢?现在我们知道它们是由夸克构成的。这就是我们所做工作的一个方面,即我们想要将物质分解开来,观察其组成部分。
但这项工作还有另一个部分,即这些部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它们之所以能组合在一起,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力。力是日常用语。在物理学中,我们称之为相互作用。所以问题是,这些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哪些相互作用?自牛顿时代以来,相互作用力就已广为人知。存在引力。贯穿19世纪,我们知道存在电力和磁力。在20世纪,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两种力。它们被称为核力,是原子弹的成因。核力。还有弱力,它导致了诸如放射性之类的现象。所以现在有四种力。
问题是,这四种力的精确本质是什么?我们通过牛顿知道引力是平方反比定律。你可能在高中物理学中学过。所以你可能会说,我们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其他这三种力是如何构建的?它们不是平方反比定律,但它们是什么?
这就是杨-米尔斯理论或规范场论的用武之地。规范场论给出了一个精确地支配这些力在数学上如何结构的原理。最初,在1918年和1919年,受爱因斯坦的启发,伟大的数学家赫尔曼·魏尔提出了所谓的规范场论。他用它来描述电和磁。那是成功的。但它不适用于另外两种力,即核力和弱力。米尔斯和我所做的就是推广了魏尔所做的事情。这就变成了一个关于力的普遍原理,解释了为什么存在这些力,包括引力。这个原理现在被称为规范原理。规范原理的详细数学结构就是我们在1954年写下的内容。
在我们写下它的时候,没有人相信它很重要。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它如此重要,但我们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而且数学结构非常优雅。所以我们发表了一篇关于它的论文。然后20年后,各种实验表明,事实上,这大约是正确的方向。之后又挣扎了五年,才清楚地表明它不仅仅是大约正确,而是完全正确。所以它变成了现在普遍接受的关于这些力是如何形成的原理。
主持人: 1954年。
杨振宁: 是的。
主持人: 你对此有何感想?事实上,50年后,你创造并提出的东西,从根本上改变了你的领域?
杨振宁: 嗯,当然,我感觉很好。但我告诉我的学生,一切事物的结构往往蕴藏着隐藏的美。如果你你能隐约感受到其中的一些美,就不要放手。我之前和你说过,1954年米尔斯和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它与实验不符,没有人相信我们。但我们看到了结构的优美之处,所以我们把它写了下来。
主持人: 结构的优雅。
物理与数学的交融
杨振宁: 没错。哦,顺便说一下,我应该补充一点,这和石溪大学有关。好的,这个杨-米尔斯理论发表了,逐渐地,最初人们并不相信它。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它的美,所以人们开始研究它。但直到70年代,它才被实验证实。所以,到了60年代,论文不多,但我想说每年都会有10篇、20篇关于它的论文。
我在1966年来到石溪大学,有一天,肯定是68年或69年,我正在做一个演讲,我正在做一个讲座,不,我正在讲一门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课程。这是一个研究生课程,我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很长的公式,一个叫做黎曼张量的著名公式。黎曼是19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黎曼张量与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有关。所以,我把这个黎曼张量的长公式抄在黑板上。当我抄写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黎曼方程的结构与我和米尔斯写下的方程非常相似。当我们在1954年写下它时,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没有研究广义相对论,所以我们没有注意到有任何相似之处。但在那个讲座中,我发现它们非常相似,所以在课后,我去了我的办公室并详细检查。果然,它们不仅仅是相似,如果你正确地定义一些量,它们就完全相同。
所以,我有点兴奋,但我不明白。所以,我去找了吉姆·西蒙斯。正如你所知,吉姆·西蒙斯是石溪分校年轻的数学系主任,他是一位伟大的几何学家。所以,他非常了解黎曼几何。所以,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们当时还在那栋旧红砖楼里,他的办公室和我的都在那里。所以,我说,吉姆,这是你非常熟悉的黎曼公式。几年前,米尔斯和我写了这个公式。看,它们非常相似。他思考了一会儿。他说,是的,是的,这并不奇怪。它们都是纤维丛。所以,我说,什么是纤维丛?
于是,他给了我一本由一位著名的普林斯顿数学家斯廷罗德写的书。书名叫《纤维丛》。所以,我带着那本书回去了,但那本书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理解的。数学家们倾向于写非常枯燥、非常生硬的陈述。它们很精确,但没有任何血肉。所以,这非常困难。全是骨头,而且不可能理解。所以,我不明白。所以,我回去找吉姆说,你看,这本书对物理学家来说毫无用处。但是我们想理解这个纤维丛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它是什么吗?他说纤维丛在数学中也是个新事物。但更早的时候,在物理学领域,从4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很多关于纤维丛的数学论文了。而且它现在是几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所以,我说,你能给我们做一些理论物理学家能听懂的讲座吗?他说,可以。
所以,他做了一系列午餐讲座,非常随意。大约有我们10个教职员工和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一定讲了大约整整一个月。这对我们很有用。所以,在那之后,我们决定送给他一份礼物,感谢他做了这些讲座。因此,我们一起凑钱,决定给他买点东西。我去找了欧文·克拉,一个我非常熟悉的数学家。我说,欧文,我们想给吉姆一份礼物。我们应该买什么?他说,吉姆不会拼写。送他一本字典。所以,我们买了一本大字典送给吉姆。他最近告诉我他还在用。
但我们在那些讲座中从吉姆那里学到的东西非常重要,不仅对我,不仅对石溪大学,实际上,它开启了一个新的趋势。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我理解了数学家们对纤维丛所做工作的要点之后,我意识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规范场论实际上都是纤维丛。所以,在那之后我立即与哈佛大学的吴大猷写了一篇论文,我们在论文中详细解释了数学家的思想和术语与物理学家的思想和术语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制作了一个小词典。这本小词典大概只有15个条目。左边是物理学家的术语。右边是数学家的术语。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精确的对应关系。所以,我们称它为词典。但是物理学家经常使用一个条目。它的专业术语叫做源。“源”实际上源于……“源”这个概念源于安培。你知道电流,3安培,5安培吗?那是以伟大的法国物理学家,19世纪的物理学家安培的名字命名的。现在,在物理学中,安培的源的概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所以,我们必须在物理学部分的字典里有这个概念。但在数学部分,我去问吉姆,你把这个叫做什么?他说,我们不处理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把它留空了。所以,这是一本字典,一边可能有15个条目,另一边有14个条目。
主持人: 并且没有任何东西对应于源。
杨振宁: 是的。但是后来,E.C.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辛格,一位杰出的数学家,来访了。我认识他,所以我给了他一份我们的预印本。他看着它,那里是一片空白。所以,他思考了一下,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他们应该处理它。他们在处理纤维丛的20或30年中,不知何故从未触及过这个想法。所以,他立即去了英国,并且他是当今英国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迈克尔·阿蒂亚的伟大合作者。现在是迈克尔·阿蒂亚爵士。那时,他还不是爵士。因此,他们研究了它,发现这个他们从未使用过的概念,但我们自从安培以来一直在处理的概念,是最有趣的。这现在成为了数学的一个新分支。
所以,他们写了一篇论文。由于阿蒂亚和辛格的声望和名气,许多年轻的数学家都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它是现代数学中一个蓬勃发展的分支。他们称它为什么?嗯,有很多名字。特别是,阿蒂亚的一个学生,名叫唐纳森,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所以,它被称为唐纳森理论。但所有这些都与那个空白点有关。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你知道,在20世纪上半叶,物理学和数学是分离的。在早期的世纪,物理学和数学是紧密合作的。但在20世纪上半叶,数学家变得越来越抽象。事实上,他们非常高兴,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个写了一篇文章说,20世纪数学的最大贡献,最大的成就是它终于从物理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说的。但随着这个纤维丛理论的发展,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又重新走到了一起。所以,如果你想问这种结合是如何发生的,我会说这与我和吉姆以及那本词典中的空白之处和石溪大学有关。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吉姆一直对物理和数学感兴趣,而且你知道他现在是个亿万富翁,他刚刚宣布将向石溪大学捐赠2500万美元。太棒了。
主持人: 所以,这只是你在生活中建立联系的另一种方式。
杨振宁: 不仅是与物质相关的联系,也是跨学科的联系。我搬回去了。我的前妻于2003年去世。我搬回了北京。正如我之前告诉你的,我在北京长大,我的父亲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清华大学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所以,我是在清华园长大的。2003年,我的前妻去世后,我搬回了清华园,现在我是清华园的物理学教授。
吉姆和玛丽莲在2001年来拜访过我们。在我搬回来之前,我就已经非常频繁地拜访那个校园了。吉姆来了,我清楚地记得发生了什么。在他拜访之后,我回来了,他也回来了,我还在斯托克拜访过他在那里的办公室。我问,你对中国的印象如何?哦,他说他对这次访问非常满意。他说,我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是贫困。在这里我看到13亿人靠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这不仅是对他们自己,也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所以,他们值得我们的帮助。你们需要什么?
所以,我说,我们在北京有很多访客,但是住房条件很差。帮我们建一些访客住房怎么样?所以,他给了100万美元,现在那个建筑群的价格在中国仍然很便宜。所以,那10亿美元,抱歉,100万美元足以建造9套非常好的公寓。它被称为陈-西蒙斯大厅,因为他对数学和物理学的伟大贡献之一是他和陈在20世纪70年代合写的一篇论文。他和玛丽莲最近去了北京,并开放了那个大厅。所以,我认为通过数学-物理学的联系,现在也存在斯托纳布鲁克-清华的联系。
东西方教育之思辨
主持人: 我想问你,你提到你从中国来到芝加哥大学时,实际上已经知道他们当时正在教的一些东西。你受到了很好的训练。您如何看待当今美国和中国在教育上的差异?
杨振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存在非常根本的差异,而这些根本差异在各个方面都有体现,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你知道报纸上说布什总统刚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如何解决美国中小学数学教育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在许多许多高中生的数学考试中,在可能有30个国家的国际考试中,美国总是垫底。排在最前面的是亚洲国家。所以,当然,这让这里的教育家和数学家感到担忧,这就是这次任命的原因。
为什么?为什么美国的高中数学教育不够好?这是因为整个教育理念和体系都不同。这里的孩子们更像是被当作成年人对待,即使他们还很年轻。在中国,如果你有一个8岁的孩子,跟他说你应该做作业,他或她就会去做作业。在这里,如果你有一个8或9岁的孩子,跟他说你应该做作业,他或她会说,我不想做。为什么不?这很无趣。这很枯燥。做作业可能会很枯燥,这个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你让一个孩子去做作业,他就会去做。
主持人: 这是纪律问题吗?
杨振宁: 是的,这是一种弥漫于环境中的纪律。所以,孩子只会做他或她感兴趣的事情,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所以,这就是区别。现在,这样做的结果是孩子们训练有素。他们做了大量的数学练习。
好吧,那么这意味着中国的制度很好吗?不,因为如果你去中国,他们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制度不好。所有的孩子都训练过度。A,他们没有空闲时间,也无法发展其他兴趣。B,他们有变得像机器人的倾向。他们不为自己思考。所以,他们正在无休止地讨论如何改变那个制度,使其更像美国的制度。
因此,在你观察了这两种制度之后,你意识到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事实上,如果布什总统问我数学界能做些什么,我会告诉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这不是教育系统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这是整个价值判断的问题。这是你如何教育的整个理念的问题。教育背后的哲学是不同的。
所以,事实上,我相信人们在各个方面所能做的就是做出小的改变,以便……这里的大多数孩子对数学不感兴趣。我会说这没关系。没有理由让这么多孩子对数学感兴趣。但这个系统必须是这样的:对于那些可能感兴趣,实际上可能非常感兴趣的人,你必须为他们提供进入的机会。另一方面,在中国,我想说不要一直训练所有这些孩子。太严格了。放轻松。是的。所以,我认为东方和美国的教育系统、教育理念的比较是一个非常有趣和非常深刻的主题。
现场问答
主持人: 鉴于你所说的一切,为什么中国的学生会来石溪大学学习?
杨振宁: 哦,主要是因为今天美国的的研究生院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在过去几分钟里谈论的是中小学。当谈到研究生教育时,美国最好的研究生院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生院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所以,我总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聪明的孩子,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她在中国的重点高中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中国的大学接受教育,并在美国接受良好的研究生教育。 我自己就从中受益匪浅。
我在中国接受了非常好的大学教育,那里的教授非常投入、尽责,他们会引导你学习困难的东西,深入研究,并涵盖广泛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来到芝加哥时,与我的美国研究生同学相比,我拥有巨大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当我来到芝加哥时,我学会了如何探索前沿领域,如何在思考前沿问题时发挥创造力。所以,我获得了两全其美的好处,我认为我很幸运,我会向任何对科学特别感兴趣的年轻人推荐这种做法。
主持人: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把话题转给我们的听众,看看听众是否有问题。如果您有问题想问杨博士,请走到麦克风前。
观众:您之前提到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验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由于各自内部复杂性的增长而分道扬镳。我很好奇您自己是如何决定进入哪个领域的,还是说这只是随着您所做的工作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你为什么决定进入理论分支?
杨振宁: 正如我所说,到20世纪中叶,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都变得非常复杂,几乎不可能同时成为两方面的专家。而且,正如我所说,费米是最后一位对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一流贡献的物理学家。
现在,就我而言,当我来到美国时,我知道我在理论方面有很好的基础。我也知道我在实验物理学方面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说,我必须拓宽我的教育基础,所以我决定我应该在这里写一篇实验论文。所以事实上,我在芝加哥的艾利逊教授的实验室里工作了大约18到20个月。艾利逊当时正在制造一台大型加速器。它大约有这个房间那么大。这是一个400千伏的科克罗夫特-瓦尔顿电路。因此他可能有五到六个研究生,而我成为了其中之一。
但我很快意识到我不擅长实验物理。当事情出错时,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出错。而且我也经常转错旋钮,对各种东西做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当靠近任何设备时,我的研究生同学们都有点担心。但我们关系很好,因为我可以很容易地为他们解决理论问题。但无论如何,经过18或20个月的工作,我非常沮丧,因为艾利森给了我一个问题。而我正在做的关于那个问题的实验进展不顺利。
有一天,泰勒来了。我在理论上一直与泰勒保持联系。泰勒说,我知道你的实验进展不顺利。我说,是的。他说,你为什么坚持实验?你已经写过一篇论文,一篇简短的论文,在理论方面。如果你把它写得稍微长一点,我可以资助它作为你的论文。所以我说,非常感谢。我得考虑一下。因为这与我长期以来的计划不符。考虑了几天后,我终于回去找他说,我接受你的建议。这在我的人生中非常重要,即了解我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
主持人: 还有其他问题吗?
观众: 我有个问题。因为石溪大学和清华大学都是世界上非常伟大的大学。作为一名教授,我教过这两所大学的所有学生。你如何比较这两所大学的学生?一个在美国,另一个在中国。谢谢。
主持人: 将中国的大学生与美国的大学生进行比较?
观众: 是的,我是指本科生。
主持人: 本科生,是的。你会如何比较本科生?您谈到...
杨振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尤其是我有一些第一手观察。我在石溪大学教过两次书,是大学一年级的物理。2004年,我在清华大学教了一个学期的大学一年级物理。所以我对这里和北京的物理专业一年级学生有第一手的了解。当然,清华是中国最难考入的大学之一。所以我发现有两个不同之处。
第一个不同之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几乎都训练有素。他们在高中做了大量的练习。所以像解析几何或三角学这样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在这里,至少我一半的学生在解析几何或三角学方面没有受到很好的训练。他们知道定义,但他们无法运用,因为他们没有做足够的练习。所以第一个区别是中国的高中训练比这里严格得多。
第二个区别是中国的学生,在清华大学的学生,非常成熟,非常有动力。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努力工作。他们有点欣赏他们想做的事情,并全力以赴。对于石溪大学的学生,我想说至少有一半人仍然在四处游荡,没有任何具体的人生目标。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这又是两种社会差异的产物。现在你不能说哪个一定更好。中国的体制更擅长培养大量会成熟的人,他们会被引导到某种生活方式中,这会使他们成为有用的公民。但美国的体制更加自由,因此,人们对生活、对一切的看法也就不那么受限制。其中最优秀的人有足够的机会让他们繁荣昌盛。看看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创造数万亿美元的价值,不仅为他的公司,也为整个世界。这种创新精神,这种自由精神,正是美国教育体系和社会所擅长培养的东西。这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我认为欧洲人、日本人,都对美国体制的巨大成功感到惊叹,它孕育了所有这些巨大的创新,并因此创造了财富。
观众: 好的,谢谢。
观众: 有问题吗?教授,您说在科学研究中感知美很重要。我想问您有什么感知美的技巧吗?您能告诉我们一些吗?
主持人: 你提到了在科学工作中感知美或优雅的重要性。你有什么技巧可以帮助你发现美或优雅吗?
杨振宁: 直接的回答当然是没有。我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美国的体制在这方面是有利的。允许自己对很多事情感兴趣,并且感知到一些事情、一些领域、一些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方向。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能够抓住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并充分发展它,这可能就是他或她发现某些事物优雅、美丽和有用的方式。
中国的体制在这方面并不好。中国的体制太倾向于强加给孩子们、学校和社会的期望,希望年轻人关注什么。并且阻止他或她拓展视野。美国体制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所以我想,当你选择讨论你想要推进的不同方向时,每种系统都有其优点和缺点。
主持人: 杨博士,非常感谢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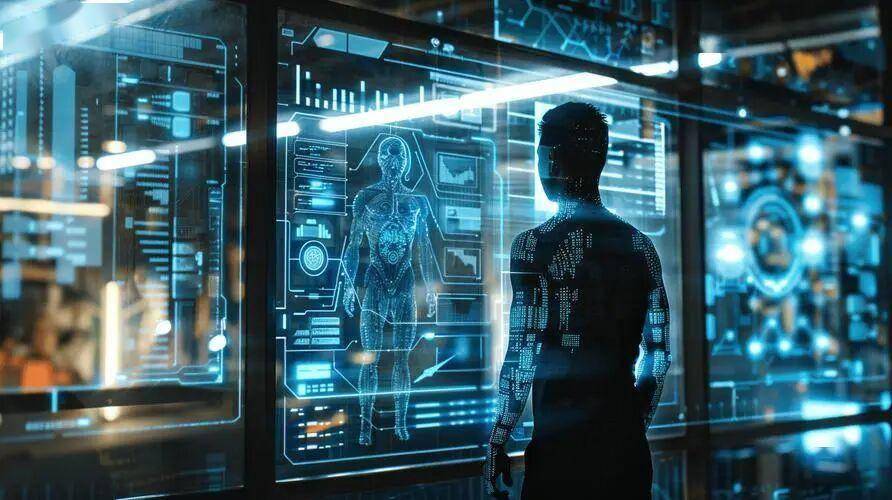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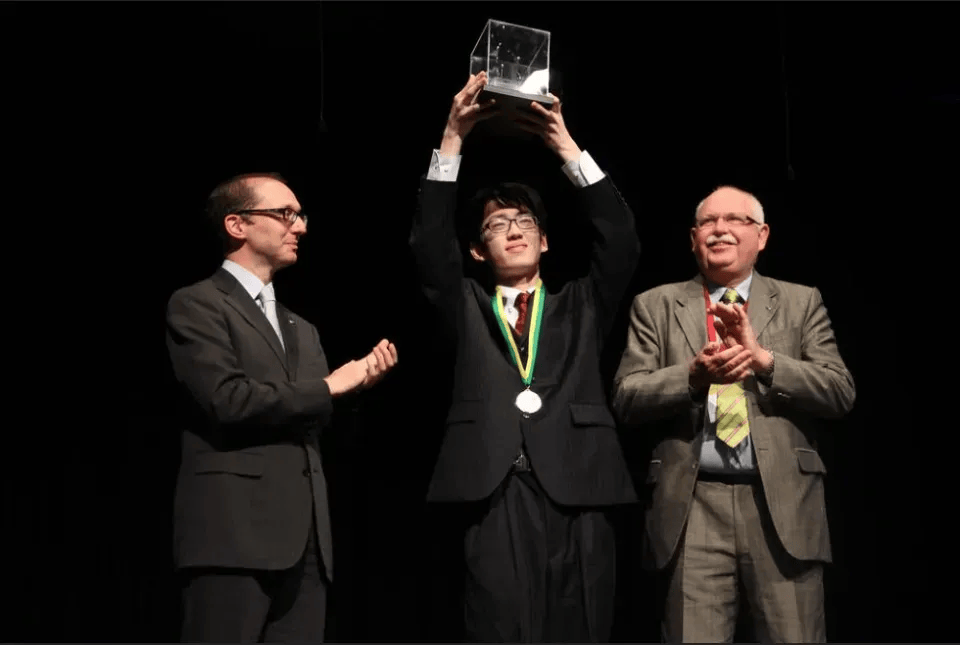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